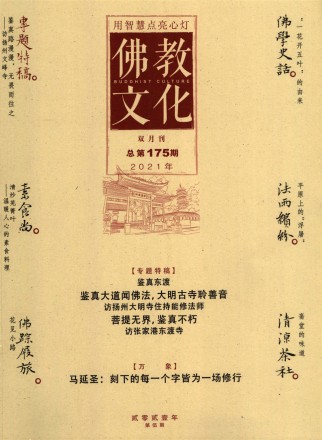佛教艺术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2 17:49:22
引言:寻求写作上的突破?我们特意为您精选了4篇佛教艺术论文范文,希望这些范文能够成为您写作时的参考,帮助您的文章更加丰富和深入。
篇1
不论是伊斯兰教的砖雕意境(尤其拱北),还是佛教造像的逼真、连廊彩绘的劝教故事,均是对自身宗教主张的彰显,以及对所提倡的敬主事人、劝善戒恶、修身养性等人生修养的明示或暗示。不论是清真寺,还是佛堂,描绘或雕饰均可见祥云、卷草、松柏、牡丹、莲花等图纹,均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具有独特风骨和风格的自然之物和文化元素的弘扬,借以宣扬其宗教价值。中卫高庙在地上殿宇墙壁上绘有卧冰取鱼、千手千眼观音来历、对犯错者的惩罚等题材的劝善抑恶的故事和形象,并附设地下建筑以模拟地狱,是为加强其教导和威慑作用;纳家户清真寺的阿拉伯文装饰,红岗子拱北的汉文对联等则是其教义和主张的直接宣扬。
2.建筑特色的不同之处
(1)建筑选址的差异
清真寺是穆斯林敬奉真主、完成宗教功课、举行宗教仪式、举办宗教知识和宗教政策宣传教育等活动的中心场所,更是广大穆斯林社会活动的中心,因此在选址上考虑便于教民每日进行五功朝拜、集会、社交、开展各种社会活动,一般在穆斯林集聚即人口稠密的地方建造,如同心清真大寺、纳家户清真大寺,体现了伊斯兰教的入世精神和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态度。拱北的建造依先贤的葬地而定,无自主选址权,如同心县丁家塘乡的周海里凡拱北。佛寺是佛教徒供奉佛和菩萨的地方,是神灵崇拜和宗教宣传的场所,也是出家僧人居住、生活和修持的地方,佛教修持的最终目的是“苦其心志,劳其体肤”而达“正定、正念、正语、正命”。“苦其心志”必先净心,因此,佛寺的选址一般远离闹市和人口稠密处,便于潜心向佛,专心修行;另外,就是选在高山峻岭间,营造出崇高、威严、神圣的“佛以山成,山以佛显”的善终意念,如须弥山石窟寺。佛教徒为了沾佛光、图吉利,总要围塔居住。而佛塔的选址就相当讲究风水、气口的畅通,如银川海宝塔。
(2)装饰图像的不同选择
伊斯兰教信奉“是唯一的造物主”,所以受崇信者唯有“真主”,而真主是无影无形的,因此清真寺、拱北等建筑中均无偶像崇拜,也没有人像装饰,甚至动物形象也是极其受限的。只有拱北中绘有凤凰、仙鹤、鹿等被赋予高洁品质和特殊寓意的少量动物形象。在装饰图腾时除特有的阿拉伯文字外,就是维美的几何图形,寓意吉祥的树草、花卉、瓜果、鸟禽等,决不会有塑像崇拜,如纳家户清真寺殿内连廊柱上的经文、围廊砖壁上的多样雕纹。而佛教建筑为弘扬和彰显“佛慈普度,众善奉行”的思想,突出佛、菩萨、天王、罗汉等具象的崇拜,所以佛庙中最重要的装饰是佛像,另通过其它动物、植物、日月星辰、祥云等的象征意义来进行寓意装饰,反映中国佛教文化的伦理思想和理想追求,如保安寺院的雕塑、梁枋的彩绘等。
(3)装饰色彩的喜好差异
沉稳的色彩使用使清真寺显得素雅、典丽,所以蓝、绿、点金是清真寺装饰的主色,使它清雅肃穆中不失华贵,如南关清真寺绿色大穹顶配以金色宝瓶顶、银色新月。再如纳家户清真寺的原色砖雕,素壁清辉,上殿内深红伴以蓝、绿、金点缀,显得庄严而华贵。而佛教建筑五彩缤纷的彩画,红、白、蓝、绿、金黄等色彩的搭配,使殿堂溢彩纷呈,如高庙廊坊柱上飘逸的飞龙、祥云,梁枋上旋子包袱的艳丽罩染,使殿堂富丽堂皇。
(4)殿宇装饰主次有别
清真寺建筑群除了围墙大门以外,主要的建筑就是礼拜大殿(或称上殿),在装饰上,也主要以门面、上殿外墙、框额为主,寺院辅房很少有刻意粉饰,以突出主体建筑物的地位和特色,如同心清真大寺、南关清真大寺等均如此。而佛堂主殿、辅殿都会有形式多样、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装饰内容。如中卫高庙三教一堂,装饰各具特色,有补充空白的观赏雕、连接或支撑构架的结构雕、主雕———佛像;物象各具情致,有昂首啸天的麒麟,有奔闹嬉戏的小鹿,有狂盛牵茎的荷叶,有嬉牡栖枝的燕雀;色彩鲜亮艳丽,有粉嫩的牡丹,翠绿的荷叶,蓝心白缘的卷云雀替等。
二、伊斯兰教与佛教建筑艺术特色差异性的原因
1.教义和信念的差别使宗教文化表现了不同的外在征象
伊斯兰教与佛教不同的宗教教义表达了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如伊斯兰教“信主独一”,而真主“非人非物”,“无物无形,无处不在”,所以真主存在于穆斯林信教者的意念中。因此,清真寺不但没有塑像,没有人像,也没有任何的人物图像,一般也没有动物、飞禽形象。而佛教则完全不同,因其教义认为:“佛是大慈大悲的人,佛是念念为众生的人,是德高望重的人,是正知正见的人,是深信因果的人,是随缘了业的人,是离一切相、修一切善的人,是露出圆满智慧的人。”可见佛是精神升华了的肉体,因此有具象表达。除了佛像,佛庙还有其他一些人像和动物装饰,如佛教壁画、碑座等,均是为了实现佛教的劝解功能,表达佛教的精神追求。装饰方面,清真寺的内殿装饰、图案搭配、色彩调制、拜毯选择均以素雅、典丽、庄重为主。因为在虔诚的教民看来,清真寺是朝拜的圣地,再穷也要养寺,如纳家户清真寺。而佛寺塑有华丽的佛像,身挂金甲。佛徒诚信“人要衣装,佛要金装”,从骨子里忠信金装的佛神力无边。佛教的建筑艺术,寄予对佛文化的宣传,通过佛、菩萨等艺术形象的塑造和善终极乐的神话彩绘,名山建寺,岩洞造佛等宣传手法,以达到对佛的敬畏以致信仰的目的。
2.文化渊源的差异决定了建筑特色的不同
我国宗教建筑受不同文化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型制、建造体例和装饰特色。佛教传入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并且因受到中国主流社会阶层的推崇而被较高程度地接纳,体现出和中国文化的高度相融性。因此,佛教建筑始终秉承中国的传统建筑风格,无论是建筑的大屋顶风格、中轴线上依次递进的院落,还是顶脊、廊柱,无论梁枋还是雀替,应用木结构或砖木混合架构,利于雕龙画凤、铸塑镂刻的工艺装饰,并且赋予了鲜亮的色彩粉饰,如中卫高庙的保安寺。而伊斯兰教自阿拉伯世界和中亚地区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较多地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因此,早期的清真寺虽受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是沿一条中轴线有次序、有节奏地递进展开,呈现一串四合院建造,但其顶部是单檐或重檐攒尖顶饰,多采用勾连达顶,将上殿逐渐扩增,而且在内部装饰中也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阿拉伯风格的拱券形装饰,如同心清真寺的米哈拉布(礼拜殿靠西墙边的一处内部看门形凹处)。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宁夏与西亚阿拉伯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穹窿顶饰的阿拉伯宗教建筑风格逐渐被吸纳并融入中国元素,新修的这些清真寺均大量使用阿拉伯建筑元素。如南关清真大寺,宏伟的绿色穹窿大顶配以金色宝瓶顶新月,成为宁夏伊斯兰教标志性建筑。可以说,宁夏伊斯兰教建筑是在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上引进西亚伊斯兰教建筑文化的同时,不断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兼容并蓄,发扬光大,并且进行了创新。其装饰艺术在推进和发展的过程中融入了中西文化的特点,如丰富变化的外观等。
篇2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6-0001-18
第464窟(张大千编号308窟,伯希和编号181窟)位处莫高窟最北端,左与第465窟,右与第463窟相毗邻,其规模在莫高窟属于中等,有前后二室。前室平顶,略有尖脊,顶部地仗大部分脱落,仅存东南角的千佛十余身。南北壁中部绘屏风式方格连环画善财五十三参变,画面受人为损毁严重,多处被切割、刻划。通往后室的西壁甬道口南北二角元代加砌坯墙,向东延长甬道,于西北角和西南角各封堵成独立的两个小方室。其中,西北角尚存半截坯墙,而西南角已荡然无存,唯地面尚存墙迹。后室绘观音三十二应化现变。
该窟形制较为反常,前室大,而作为主室的后室反而小(图1),有违常制。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学界存在着两种推论,其一,“推测可能非一次性完工,后来凿设后室时限于条件而未能挖掘成大于前室的后室”。其二,“从目前窟前崖面现状看,现在的前室门外凿崖为北、西、南三堵陡立的平面壁,西顶呈披形,表明原为一个窟室,可能是前室,后随崖体一起坍毁,或许原来是半石崖半木建组构的前室或窟崖,今毁失。今之前室则为原来的主室”[1]。后一种推测得到了考古学成果的支持[2]。原前室塌毁之遗迹至今依稀可辨。
一 张大千的记述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先生曾对莫高窟北区包括第464窟在内的洞窟进行过挖掘,认为第464窟为“西夏、回鹘修”,对窟中内容作了如下叙述:
回鹘佛经故事
北壁,二十方,每方间以回鹘文字,高六尺,深一尺六寸半。
南壁,十九方,每方间以回鹘文字。
南壁,佛经故事,东端上书“唵嘛弥把密吽”印度等四种文字。
北壁,佛经故事,东端上横书印度等三种文字,下书:“语行无常,是法生灭”①、“唵嘛尼把密吽”。
又回鹘文字:“生灭灭己,寂灭为乐。”
西夏人画菩萨,一区。外画一圆形。西壁正中、上。
观音、普门品二十方,每方高二尺,广二尺一寸。西、南、北三壁
佛,四区,龛顶、四面。
又,一区,龛内、藻井。
回鹘人画菩萨,二区。高三尺四寸,龛门、两旁。
又上有佛各二区,外画一圆形,并有回鹘题字。
贤劫千佛,龛门、顶。
回鹘文,两方,高四尺三寸,广一尺五寸。剥落,龛内东壁、左右
印度文“唵嘛尼把密吽”,四寸大。龛内东壁上、间以花枝。[3]
张氏所言第464窟为“西夏、回鹘修”的问题比较复杂,将于下文详述,这里仅就张氏对窟内壁面题字记录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略作申述。
其一,前室南壁“东端上书‘唵嘛弥把密吽’印度等四种文字”,由上至下,依次应为用梵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书写的六字真言(图2)。
其二,前室北壁“东端上横书印度等三种文字,下书:‘语行无常,是法生灭’、‘唵嘛尼把密吽’。又回鹘文字:‘生灭灭己,寂灭为乐’”(图3)。所谓“三种文字”,由上至下,依次为梵文、回鹘文和藏文。其下文字,张氏所述有误,应改为:
其下中间为汉文与八思巴文合璧书写“唵嘛尼把密吽”右书汉文“语行无常,是法生灭”,左书汉文“生灭灭己,寂灭为乐”。
八思巴文创制于忽必烈时期。忽必烈尊崇藏传佛教,以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命他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新的蒙古文字,以取代原来流行的回鹘式蒙古文,故称“蒙古新字”,又称“蒙古国字”,俗称“八思巴文”。至正六年(1269)二月,这种新文字正式颁行全国。八思巴文是一种拼音文字,绝大多数字母仿照藏文体式而呈方形,少数字母采自天城体梵文,还有个别新造字母。这种文字虽作为蒙古国字颁行全国,但未能真正推广下去。除去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而且不如回鹘式字母更适用于蒙古语的语言特点,因为蒙古语毕竟和回鹘语一样,同属阿尔泰语系,均为黏连语。质言之,八思巴文的创制既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也有违民族语文发展的自然规律,因此,尽管八思巴文名为官方文字,但民间依然使用汉字及回鹘式蒙古文,故其流行不到一个世纪,便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了[4]。
另外,梵文六字真言的顺序应为O mani padme hūm,但在第464窟前室北壁中似乎有书写混乱之嫌,如尾字hūm(吽)被单写于第1行,另行开首写倒数第五字dme(弥),然后再写O mani pa(唵嘛尼把)。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二 西夏石窟说驳议
关于第464窟的时代,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先生即言该窟为“西夏、回鹘修”[3]628-629,已如前述。至于何以如是断代、定性,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后室西壁有所谓的“西夏人画菩萨……观音、普门品……佛”。此后,学界多认为该窟为西夏窟,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谓“西夏窟(元重修)”①。是后,学术界多接受西夏说②。近期,西夏艺术史专家谢继胜再撰文考证,认为第464窟为西夏窟,并以之为据,证明风格与之相近的第465窟亦为西夏窟[5]。
另一种意见则反对西夏说,如西夏石窟考古专家刘玉权在前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于1982年完成了对西夏洞窟的分期,从敦煌石窟中分出属于西夏时期的洞窟88个,其中莫高窟有77个,榆林窟11个,但第464窟未被列入其中[6]。后来,刘先生对原先的分期再作修订,将西夏洞窟分为二期,其中前期65个窟,后期12个窟,仍未包括第464窟[7]。对刘先生分期持有异议的关友惠先生,同样也将第464窟排除在西夏窟之外[8]。梁尉英先言其为“元代早期的洞窟”[9],后又改称“西夏洞窟”[1]。王惠民言西夏说“尚待进一步确定”[10]。
总之,学界对第464窟的分期存在西夏窟和元窟两种说法,而以西夏说占主流。那么,西夏说之依据何在?却一直是个谜,因为从洞窟现存壁画中除了所谓的具有“西夏特点”的上师莲花帽之外,看不出西夏石窟的任何特征。谢继胜先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考察既有的研究成果,并特意向敦煌研究院有关人员咨询,得到了如下结果:
通读梁[尉英]先生的论文,作者并没有明确说明第464窟定为西夏窟的依据是什么。主室的壁画究竟是西夏壁画还是元代壁画?笔者在兰州访问梁先生时,先生亦语焉不详。笔者请教敦煌研究院负责清理北区石窟的彭金章先生,他说第464窟壁画是否为西夏壁画他不能断定,但第464窟的建窟时间比画面题记显示得更早,有可能建于北魏。此外,笔者还就第464窟壁画请教西夏壁画研究专家刘玉权先生,刘先生称早期确认此窟是西夏窟,但哪一部分壁画是西夏壁画仍不清楚,现在的壁画可能是元代壁画。[5]70
可见,言第464窟底层壁画为西夏者众,但拿出真凭实据者鲜。有鉴于此,谢氏著专文对该窟进行研究,确认该窟为西夏壁窟。遗憾的是,同样未举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其主要证据有四,其一为前室南北壁所见两则来自“大宋”的游人题记。
前室北壁西段题记,刻划,文曰:“大宋阆州阆中县锦屏见在西凉府贺家寺住坐游礼到沙州山寺梁师父杨师父等。”①阆州阆中县即今四川阆中市,宋代隶属成都府路,南距合川市约120千米。
前室南壁西段题记,刻划,文曰:“大宋府路合州赤水县长安乡杨到 此 寺居住沙州……”②其中的合州治今四川合川市,所辖赤水县地当合川市西北65千米赤水乡,同隶成都府路。所以题记中的“府路”应为“成都府路”。
二题记书写者皆来自今四川省合川县北或西北,其中又都出现“杨”姓人士,书写位置分处北壁和南壁西段,大致对应,开首皆称“大宋”,很可能为同行者所书。这些题记不仅不支持谢氏所主西夏说,而且可看作谢说的反证。谢氏辩论说:“这些题记的年代都是在北宋年间,很可能是西夏据有敦煌之后不久……西夏据有敦煌后,敦煌地方仍然使用正统年号,但这种过渡时间大约只有10年左右,其典型例证就是莫高窟第444窟,当时西夏据有敦煌已10年,但窟内题记仍用中原王朝年号。”[5]71谢氏接受的是西夏于1036年正式统治敦煌之说,且不论此说是否可以立足③,单就以“大宋”题记来证明西夏窟的存在而言,在逻辑上就有些不通了。论者或可作如下辩解:西夏于1036年统治敦煌后,势力尚不稳固,故允许沙州回鹘继续向宋朝贡,敦煌石窟中出现大宋年号,也是西夏统治力量薄弱所致。如果此说不误,敢问西夏在敦煌统治尚不稳固的初期,朝不保夕,怎会有余力和心思来修建规模如此宏大的石窟呢?论者还可继续辩解:正是由于西夏统治不稳固,所以对第464窟壁画的重绘并未下大工夫,只是在素面上重绘而已。果若如是,那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战乱期间虔诚的西夏佛教徒可以作的佛事,何以至西夏统治稳固后却不能继续,以至于半途而废呢?不可思议。谢氏所举证的二题记不仅不支持西夏说,而且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依常理,一般会视之为西夏未能对敦煌实施有效统治的佐证。
谢氏的第二个论据是第464窟壁画具有比较典型的藏传壁画特点。我们知道,西夏早期佛教主要受回鹘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影响④,故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所见早期西夏壁画不管在题材、布局、人物形象、衣冠服饰,还是在绘画技法上,都全面继承北宋壁画之余绪,上与曹氏归义军所设地方画院及其后的沙州回鹘洞窟相衔接,具有严谨的写实作风,但构图显得过于程式化,经变故事情节简略而显得呆板。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特色,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人物形象逐渐接近党项族的面部与体质特点,西夏所流行的服饰在壁画中开始出现。至于藏传佛教的影响进入洞窟,藏式绘画开始流行,已是晚期之事①。西夏与藏族尽管早有接触,但藏传佛教在西夏流行,则始自西夏仁宗仁孝统治时期(1140—1193)[11]。谢继胜明确指出:
到12世纪末,西夏人已经完全将藏传绘画与本土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创造了一种新的样式,笔者称之为“西夏藏传风格”,这种风格的出现标志着西夏具有了可辨识特征的自己的艺术风格。
第464窟壁画即具有比较典型的笔者所谓的西夏藏传壁画特点。[5]74
依上述引文,第464窟已经具有“西夏藏传壁画特点”,自然为12世纪末以后之遗存,而谢氏在同文中又言:“通过对莫高窟第464窟游人题记年代的分析确认该窟壁画绘于西夏前期。”[5]79到底该窟壁画属于前期还是属于后期呢?显然自相抵牾。
谢氏确认第464窟为西夏窟之第三个证据为后室南壁所绘上师所戴帽子为宁玛派的莲花帽(图版1),此为其立论的最根本依据。除该窟外,这种帽子在莫高窟第465窟、榆林窟第29窟均有出现,几乎完全一致。榆林窟第19窟甬道北壁有汉文刻划题记:“乾祐十四年日甘州住户高崇德小名那征到此画秘密堂记。”②乾祐二十四年,即1193年,而“秘密堂”则为人们对以藏密佛窟或佛寺的一种称谓。第19窟题记所谓“秘密堂”,据推测即榆林窟第29窟。如果此说不误,那么榆林窟第29窟的营建年代即应在夏仁宗乾祐二十四年(1193)[12]。另外,在酒泉文殊山万佛洞、瓜州东千佛洞第4窟、千佛洞第7窟、宁夏山嘴沟石窟、宁夏拜寺口西塔、黑水城出土唐卡等西夏上师像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莲花帽。但是,这种莲花帽并非西夏所特有,原本为8世纪入藏的印度佛教大师莲花生所戴之冠,后演变为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传统着装[13],诚如谢继胜先生所言,“西夏以后的作品也同样出现着莲花冠的上师像”[5]76,不仅元明清代有所见,甚至出现于16世纪尼泊尔的绘画中,直到今天,宁玛派上师仍佩戴这一形式的莲花帽。故这种着莲花帽上师像的出现,不足以支撑西夏说的成立。
第464窟被定为西夏窟的第四个证据是后室窟顶藻井的大日如来像。该窟窟顶绘五方佛,东西南北四披四位如来均为汉地绘画风格,但中央的大日如来却为藏传绘画风格(图版2)。这种画法在西夏绘画中极为多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藏传佛教艺术中,这种画法一直盛行不衰,非西夏所特有,同样不足以证明西夏说的成立。
第464窟之所以被定为西夏窟,还有一个潜在的理由,即该窟有多处西夏文题记。据有关人员调查,窟中现存西夏文题记7则,其中5则用硬物刻划,二则用粗笔墨写[14]。一般而言,硬物刻划文字不可能出自石窟创建者之手,而是后来朝山者的随意题写。二则墨书题记,都很简单,总共只有5个字,显然亦非创建者所书。正如刊布者所言,以上7则题记均为“巡礼题款”。这些题记多书写于前室南北壁的西端素壁上,与前述“大宋”汉文题记并书,后均为加长的甬道所覆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室东壁甬道顶部书有梵文六字真言(图4),读作:O mani padme hūm(唵嘛尼把密吽,又见于前室南北二壁),与壁画浑然一体,属于同一时代之物。它的存在直接否定了西夏说。
在藏传佛教中,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又被称作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咒,只要常念这神奇的咒语,即可获得现报,修持方法极简单易行。14世纪成书的《王统记(Gyalrab Salwai Melong)》以《白莲花经》①的基本思想为基础,对六字真言所体现的观音法力作了如是概括:
此六字咒,摄诸佛密意为其体性,摄八万四千法门为其心髓,摄五部如来及诸秘密主心咒之每一字为其总持陀罗尼。此咒是一切福善功德之本源,一切利乐悉地之基础。即此便是上界生及大解脱道也。[15]
作者把这六个神奇的字与佛教的“六道”理论结合了起来,认为六字与“六道”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唵”,除天道生死之苦;“嘛”,除阿修罗道斗诤之苦;“呢”,除人道生老病死之苦;“叭”,除畜生道劳役之苦;“咪”,除饿鬼道饥渴之苦;“吽”,除地狱道寒热之苦。[15]21
这样,六字真言也就差不多成了佛法的象征,几乎涵盖了佛教的众多精义。这种解释虽有点背离梵文的原始意义,但极大地神化了六字真言的不凡法力,而且将六字与“六道”巧妙地附会在一起,更容易为信徒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对六字真言的信受奉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信众之外,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②。
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出现的最早证据,可追溯到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在那个时代书写的古藏文文献中,即已发现有用吐蕃文书写六字真言的情况,如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S.T.420-1、S.T.421-1、S.T.720[16]及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P.T.37、P.T.51等藏文写卷即是[17]。这些写卷尽管有的已很残破,而且写法也不无差异,但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至迟在8—9世纪时,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即已出现了。此后,随着藏传佛教在后弘期的迅猛发展,六字真言也开始逐步流行起来,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则应自元朝始[18]。
就西夏而言,在为数众多的藏传佛教画品中,六字真言迄今尚无所见,榆林窟第29窟为西夏窟,窟顶藻井井心有墨书梵文六字真言,但为元代之遗墨[19]。说明那个时代六字真言在西夏尚不流行。而第464窟之梵文六字真言与壁画作于同时,则该窟非西夏窟可明矣。
综合以上各因素,足证西夏说是缺乏根据的,难以成立③。
三 原窟为北凉禅窟
那么,第464窟应创建于何时呢?近期的考古资料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考古资料证明,第464窟原为多室禅窟,前室(即原来的主室)南北二壁原各开两个小禅窟(图5)[2]54-56。
众所周知,莫高窟禅窟的开凿主要在隋代以前,隋以后开窟虽多,但均为功德窟,未见到一所禅窟。
莫高窟现存洞窟中,最早的禅窟为第268窟。敦煌研究院过去将第268窟主室南北侧壁的四个小龛分别编为第267、269、270、271窟(图6)。从整个洞窟结构看,四个小龛均属第268窟之组成部分,故应视作一个窟来看待。这四个小龛面积很小,“才容膝头”⑤,是禅室无疑。全窟仅正壁及窟顶有造像,侧壁及两侧禅室皆无造像,整体窟室结构保留了西北印度地区禅窟与设像处所分离的原则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第270窟暴露出来的层位关系看,这一组窟龛经过了两次重修,现存第一层是隋画千佛(第268窟西壁未重画),第二层是北凉时期(401—439)画的金刚力士和飞天等,与第268窟西壁下的供养人属于同层。在北凉画下有一层白色粉壁,无画,是证该窟原本即无壁画,供禅僧坐禅苦修之用[20]。其开凿时代被定为北朝第一期,即北凉统治敦煌时期(420—442)②。
属于北朝第二期(即北魏时期)的禅窟有第487窟。该窟由前室和后室两部分组成,其中前室现存部分呈横长方形,从残存遗迹看,原为面阔三间的窟檐式建筑。主室平面呈方形,中部偏西筑有方形低坛,南北二侧壁各凿出四个小禅室③。
属于第三期(即西魏时期)的禅窟有第285窟,堪称莫高窟禅窟中最为典型者。该窟南北二壁各营建小禅室四个(图7),该窟北壁东起第一铺滑黑奴造无量寿佛发愿文的纪年,可以证明第285窟完成于西魏大统五年(539)或稍后[21]。
上述诸窟小禅室面积都很小,不足半平方米,仅能容一人打坐,室内亦无色彩粉饰,仅用泥轻抹而已,禅僧们面壁打坐,寓示四大皆空,无所执著。入静一无所求,出静则绕佛坛念佛,故满室饰彩壁画,昭示着美妙的极乐世界,通过鲜明的比照使禅机得到进一步升华[22]。而窟内壁画中的禅定比丘列像,“并不是表现修行中的比丘,更大的可能性是表现步陟禅定修行阶梯,最终获得阿罗汉果,得到了神变的高僧神僧”[23]。
此外,与之相仿的还有新疆吐鲁番吐峪沟北凉第42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4窟)。该窟窟顶呈纵劵顶,平面为长方形,后壁开一禅室,东西两侧壁各开两禅室(图8),内绘比丘禅观图。值得注意的是,该窟纵劵顶两侧壁有三排比丘禅观图。所绘内容和十六国时期流行的禅观思想息息相关,所依禅经主要有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和《禅法要解》④。日本学者山部能宜通过图像与经典的比对,认为第42窟之壁画与424年畺良耶舍译《观无量寿经》最为接近,但又不尽相同,应含有中亚地方因素①。若此说成立,那么第42窟之开凿应在424—460年之间②。
综观以上所列禅窟,北魏第487窟与西魏第285窟之形制基本一致,均在主室侧壁各开4个小禅室,而北凉第268窟和吐峪沟同时代第42窟则更为接近,各于侧壁开2个小禅室,与第464窟所见几无二致。考虑到隋代以后未见有禅窟开凿,故可将第464窟始造时代推定在北朝时期,若再考虑其形制特点,似定为北凉窟较为稳妥。
北凉时期,在敦煌禅修的僧人数量应是较多的,仅有第268窟的4个小禅窟显然不够用,20世纪末北区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莫高窟用于修禅的石窟多在北区。莫高窟北区现有石窟248个(含敦煌研究院编号第461—465窟)其中专供僧人修行习禅用的石窟就有82个,另有5个僧房窟附设禅窟[24]。其中,B125窟为一单禅室窟,树轮校正年代为420年,被推定为北凉时期[25]。B113为一多禅室窟,形制与吐峪沟石窟第42窟几乎完全一致,亦当为北凉窟[26]。说明自北凉始,莫高窟北区即为禅僧修行的集中区。
总之,可以看出第464窟最初开凿于北凉时期,原为多室禅窟。此后长期被废弃,及至元代,通往禅窟的甬道被封堵,多禅室窟遂演变为毗诃罗窟。随着前室的坍塌,原来的中室变成了前室[2]54-56。
四 出土文献及相关问题
自20世纪初以来,第464窟出土了大量不同文字的文献。在敦煌莫高窟所有洞窟中,除藏经洞之外,以该窟出土文献最多,故有“第二藏经洞”之称[27]。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曾造访该窟,将其编为181窟,并于洞中清理出不少文献,约有600件左右。他在笔记中写道:
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蒙古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这是一种新奇事。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纸页,他们至少属于4部不同的书籍。[28]
继伯希和之后,张大千先生于1941—1943年进驻敦煌,逗留莫高窟期间,曾对北区部分洞窟进行了非科学性挖掘,获得回鹘文、西夏文、汉文、蒙文等文书百余件,原为张大千个人收藏,后携往域外,其中相当一部分现收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构成了该馆收藏敦煌文献的主体[29]。如编号为180-ィ1“敦煌遗片”一册共8叶,其内收有西夏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佛典写本或刻本断片;编号222-ィ63则为“西夏、回鹘文书断简”一册,共18叶,其中主要是回鹘文文献;编号183-ィ279为“西夏文断简”一册,有近百文书整叶和残片,经张大千先生重裱成44叶。在日本藤井有邻馆和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中,也有一些来自敦煌,但并非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的回鹘文文献。据研究,这些文献大多都应出自莫高窟第464窟③。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对该窟进行了系统发掘,又获得了90余件古代文献。
第464窟出土文献经过整理研究,今已大体明确,以印本居多,大多属元代之物。
前人多言,前室有双层壁画,底层为西夏画,外层为元画。笔者仔细观察,却看不出哪个地方有重层壁画之遗痕。该窟内容复杂,为清楚起见,这里将其分作三个层面来叙述。
其一为第464窟之原始形态,建于北凉,为禅窟。但有无绘画已看不出,从现存壁面观察,当时无画,应为素壁。
其二为后室,北、西、南三壁前设佛床,但塑像今已荡然无存,唯壁画保存完好,具有显密融合的艺术特点,明显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其三为前室与甬道。后室甬道原来仅为0.90米左右,后来向东加长为2.50米,在西南角和西北角各构成一个封闭式方室,然后绘制壁画。从画面看,甬道二壁、甬道加长部分二侧壁与前室南北壁壁画是浑然一体的,不管是线条、着色还是晕染法以及前室窟顶与甬道顶部所保存的千佛造像,都是完全一致的,无疑完成于同时。
加长甬道以构成独立的小方室,这种情况在莫高窟极其罕见。何以如此?值得深究。
众所周知,二方室之内各围一废弃的小禅室,其中西北角的小禅室后来成为瘗埋“元代公主”之墓(图5)。1920年,滞留于莫高窟的沙俄残部,曾对该墓进行了盗掘,将其中的珠饰钗钿洗劫一空[47]。唯留一只“公主”脚,至今尚存于敦煌研究院[48]。至于“元代公主”之由来,史无明载。在莫高窟北区,用于瘗埋僧人骨灰、遗体和遗骨的瘗窟有25个,其中15个是专门为瘗埋死者而开凿的瘗窟,另有7个窟是改造原来的禅窟而成[24]346-347。第464窟“公主墓”显然属于后者,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第464窟规模与通常的瘗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若没有特殊且尊贵的地位,是不可能获此殊荣的,尤其是当时为了掩人耳目,竟对石窟整体结构进行了改造,将原来的甬道加长一倍以上,将公主墓完全隐藏了起来。由是以观,“元代公主”墓之说当非空穴来风,而是可信的。公主身份高贵,随葬物较多可想而知。为保持一致,在石窟前室西南角也修建了同样形状的方室。
1908年,伯希和对第464窟进行了考察,并予以清理,获得众多文物。关于该窟的内容与时代,他作了如下叙述:
过道中每个壁面的装饰主要由占据了洞窟整个上部的一幅画组成,它约有3米长,位于a、b之间,被分成由冗长的蒙文引文分隔开的斜长的小画面,而这些引文一般均写作红色,唯有引文开始处得标题系用蓝色写成,所有的题识都写于黑色底面上。这一切绝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它们原来是组成长篇蒙文和藏文写本的叶子,而那些绘画则相当于在内部装饰了夹板的两个版面的细密画。有关这种装饰(它也是过道中和洞子中的装饰)的时代,我们掌握有如下论据:它覆盖了一个石灰粉刷层,后者上面就写满了西夏文(同时还有藏文和汉文)游人题记。因此,它肯定是元代的。[28]374
伯氏依石窟中的蒙古文题记,且题记书写于壁画营造之初,从而确定该窟为元代之物。这一断代是可信的,但必须指明一点,其中的文字为回鹘文而非蒙古文。伯希和精通回鹘文,可能是时间紧迫,加上题记多模糊不清,导致伯希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这一误判并不动摇其断代的根基。
伯氏依题记对石窟的断代之法为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所接受,他进一步引申说:
由伯希和图录观之,第181窟壁面上的回鹘文,并没有后世不断添加或涂鸦的痕迹,而是在营造之初与壁画同时写上去的。这是不会错的。有一藏文题铭,观其与壁画之关系,倒可定为后世添加物。故而,若将第181窟定于西夏时期(并非开凿),那窟中会存在与壁画相一致的回鹘文榜题也就匪夷所思了。所以,还应遵从伯希和的推断,认为是在“蒙古统治时期”的看法是妥当的。[49]
应该说,森安的思考也是有根有据的,遗憾的是,他并未意识到第464窟的壁画是双层的,表层为元代,本无异议,但还有底层壁画。森安为肯定该窟为回鹘窟,为否认西夏因素的存在而断定第464窟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也为蒙元时代回鹘人使用之物[50]。似乎大可不必。关键还在于窟中的题记,如伯氏所说,这些题记与壁画形成于同一时间,故题记的释读对壁画的断代与定性势必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上文释读的三则题记,反映的是四地、五地和十地菩萨,九地菩萨虽榜题毁失,但图像犹在。《法门名义集》云:“圣种性有十地菩萨,自此已后是出间圣人之位。”[40]202从窟中现存遗迹可以看出,甬道二壁所绘恰为十尊菩萨,合为“十地菩萨”,除现存4尊外,其余6尊皆因土坯所砌甬道的被毁而残缺,如北壁甬道现存部分呈曲尺形,下边长2.50米,上边残长0.90米(图版8),就是明显的例证。
其中,一至五地菩萨位于南壁,自左向右依次排列;六至十地菩萨位于北壁,自右向左依次排列。从1908年伯希和所摄照片看,西北角和西南角的两个方室当时即已被拆毁[50],原作为方室建筑一部分的甬道南北二壁延伸墙壁上的菩萨像也随之毁于一旦。
依据甬道十地菩萨榜题,结合窟内随处可见的其他回鹘文题记,势必需将之与回鹘相联系。考虑到前室二壁中的四体六字真言和五体六字真言的存在,加上洞窟中出土的文献绝大多数为元代之物,可以认为,第464窟前室及甬道现存壁画应出自回鹘之手,为元代之画作。而元代也是回鹘在敦煌比较活跃的时期。
至于画风问题,因本人对石窟艺术素无研究,故特向敦煌研究院西夏、回鹘壁画研究专家刘玉权先生求教。刘先生言:第464窟壁画明显不属于西夏,而有回鹘画风特点,但由于与他辨识出的23座沙州回鹘洞窟差别甚大,故在分期排年时,将第464窟排除在沙州回鹘窟之外。刘玉权当时确认的沙州回鹘洞窟计有23座,分为前后二期,兹引录如表1:
其中第237窟(张编53窟)、309窟(张编98窟)和310窟(张编99窟),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已被张大千确定为回鹘窟[3]124-126,222-224。另外,莫高窟第368窟(张编172窟)也曾被张大千确定为回鹘窟[3]250-251,但在刘玉权的分期排年中却被排除在外。刘先生所列第23窟,其时代应在11世纪70年代以前,这时的回鹘完全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堪称汉传佛教在西域的翻版[52],而第464窟壁画却不同,后室明显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前室与甬道绘画尽管以汉风为主,无明显藏传佛教绘画特点,但与上述所列第23窟绘画之画风亦迥然有别,乃时代变迁与文化变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看来,张大千将第464窟定为“回鹘修”当是颇有见地的。除壁画外,张氏所作结论似乎还肇基于该窟内西夏文、回鹘文题记之众多。前文已指出“西夏说”之非,此不赘述。但其中的回鹘文题记当是与壁画同时共生的,非后人所题写,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就这一点言,张氏的结论是颇有见地的。
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敦煌偏处西北,何来“元代公主”之葬呢?恐还需从瓜沙地区的统治者——蒙古豳王家族与敦煌石窟的关系中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蒙古于1227年占领敦煌,“隶八都大王”[53]。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元政府设瓜沙二州,隶肃州,归中央政府管辖,授当地百姓田种、农具。十七年,沙州升格为路,设总管府,统瓜沙二州,直接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十八年正月,“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54]。是后于至元二十四年始筑沙州城,“以河西爱牙赤所部屯田军同沙州居民修城河西瓜、沙等处。”[55]4年后,以政局不稳,元政府尽徙瓜州居民入肃州,瓜州名存实亡。这一时期,瓜沙之地位渐趋衰微,直到大德七年(1303)随着蒙古大军的屯驻,局面才得以扭转。《元史》卷21载:
[大德七年]六月己丑,御史台臣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56]
是时,“甘州军隶诸王出伯”[57]。出伯与其弟哈班均受赐金印,以诸王身份出任河西至塔里木南道方面军事统帅重任,节制甘肃行省诸军。大德八年,“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59]461。蒙古崛起朔漠,肇兴之初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因此诸王初无位号,仅有六等印纽的赐予,中统以后才开始以国邑之名封号,但仍以六种印纽分等[58]。威武西宁王位列诸王第三等,佩金印驼纽。大德十一年,出伯进封豳王[59],由三等诸王晋升为一等,佩金印兽纽,由甘州移驻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豳王乌鲁斯得以正式形成。接着,天历二年(1329)出伯子忽答里迷失(又作忽塔迷失、忽答的迷失、忽塔忒迷失)被封为西宁王,佩金印螭纽,位列二等诸王,驻于沙州(甘肃省敦煌市)。是年十二月,忽答里迷失进封豳王。[60]翌年,西宁王之位由其侄速来蛮继袭①。元统二年(1334)五月,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袭其旧封为威武西宁王[61],地位次于西宁王,佩金印驼纽,驻于新疆哈密。出伯兄哈班之后宽彻于天历二年八月被封为肃王[60]739,位同豳王,为一等诸王,佩金印兽纽,驻于瓜州(甘肃省瓜州县)[62]。本文所谓的豳王家族即为豳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和肃王的总称。有元一代,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名统领镇戍诸军,防守西起吐鲁番东至吐蕃一线。
蒙古大军入驻后,瓜沙社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发展,莫高窟、榆林窟的佛事活动也在元代晚期渐趋高涨。至顺二年(1331)瓜州知府、瓜州郎使郭承直与其子郭再思、司吏吴才敏、巡检杜鼎臣等巡礼榆林窟,是元代最早的纪年题记②。西宁王速来蛮镇守沙州,于至正八年(1348)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碣》,率领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诵经奉佛[63]。三年后,速来蛮又主持修复莫高窟文殊洞(第61窟)外的皇庆寺[63]112-116。在莫高窟现存的10个元代石窟(第1、2、3、95、149、462、463、464、465、477窟)中,大多都属于晚期。至正十三年,守镇官员下令重修榆林窟③。榆林窟的4个元窟(第3、4、6、27窟),都建于元代晚期。
由于蒙古统治者如同西夏晚期统治者一样推崇藏传佛教,自西夏以来即流行于敦煌的藏传佛教得以继续发扬光大,故莫高窟现存的藏传佛教艺术除去西夏传下来的汉密画派(如第3窟和61窟甬道)之外,又有风格迥异的金刚乘藏密画派(如第465窟)[64]。在莫高窟、榆林窟现存14个元代洞窟中,又以属于晚期者居多[65],故学界认为“元代晚期方是莫高、榆林二窟修建的高涨时期”[66]。这种局面的形成,盖与瓜沙地区统治者豳王家族在敦煌大兴佛事有关。对此,笔者拟另文详述,兹不复赘。前文述及的“元代公主”,很可能就是豳王家族成员之一。如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所显示的那样,豳王家族成员有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称号几同于中原大汗。说明诸王之女也被称作公主[63]108-112。曾出家为尼的某公主,亡后瘗埋于第464窟。否则,敦煌何来公主呢?而亡于他地,并未在敦煌出过家的中原大汗之女绝不会千里迢迢而远葬西北边陲之地敦煌。
有元一代,回鹘与蒙古王室关系密切,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被成吉思汗封为第五子,享受诸王待遇,并嫁公主[67]。是后,回鹘人中大凡“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68]。豳王家族“兼领瓜沙以西北至合剌火者畏兀儿地征戍事”[69],与回鹘关系同样非常密切,故酒泉文殊山石窟发现的著名碑刻——汉—回鹘文合璧《重修文殊寺碑》记录了豳王家族兴修文殊寺的事迹,碑主为第三代豳王喃答失太子[70]。作为蒙古人,碑文不用蒙古文,却使用汉文与回鹘文。至正十二年(1352),来自哈密的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赴榆林窟朝山,题写的文字也是回鹘文而非蒙古文,均体现了回鹘与豳王家族关系之特殊性。前已述及,第464窟出土文献差不多均为元代之物,凡纪年明确者,皆属14世纪的早期和中期,其中Or.8212-109回鹘文《吉祥胜乐轮》甚至是奉沙州西宁王子阿速歹(Asuday)之命而抄写的[71]。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本(北大D154V和北大附C29V[72])中还有两首赞美西宁王速来蛮的回鹘文头韵诗,证实当地回鹘佛教与豳王家族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73]。其出土地点虽不详,但依早期发现元代回鹘文文献的情况看,应以第464窟可能性最大。
其时当在元朝的后半,正值莫高窟营建之高涨期。第464窟由回鹘修复,窟内却瘗埋着蒙古豳王家族的公主,那么,回鹘之修复活动则必与豳王家族息息相关。易言之,豳王家族应为该窟的供养主。
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后室东壁即甬道西口南北二侧壁之壁画在保存完好而且非常清晰的情况下曾被人粉刷过,覆盖后题以回鹘文文字(图版9)。其中,南侧满壁书文字29行,北侧第1行文字未及写完便戛然止笔了,显然系受外力影响而中断。何以如此?令人费解,或许只有那些已完全模糊不清的回鹘文文字能够告诉我们原因,遗憾的是这些文字今天已完全无法辨识了。笔者个人臆测,应为功德记之属,期待着来日能有办法释读出这些文字,为疑团的解决提供些许信息。
在敦煌石窟营建过程中,未竣工而突然终止的情况时有所见,尤其是在北朝、五代等战乱年代更是常见。致其生变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改朝换代始终居于首位,第464窟之情况当亦属同样因素所致。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于同年攻陷元都大都,元朝灭亡,但瓜沙二州尚处于蒙古豳王家族统治之下,第464窟前室南壁东段墨书“至正卅年(1370)五月五日”[74]即是明证,因为至正二十八年元朝即已灭亡了,但瓜沙地区仍行用元朝年号。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遣冯胜率大军经略河西,在瓜沙击败元朝留守河西军之残部。第464窟之修复活动之所以功未竟而突然中止,当与这场变故有关。能够对我们这一解释提供佐证的是第464窟大批回鹘文木活字实物的发现。1908年,伯希和于此窟掘获回鹘文木活字968枚,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又发现19枚。这些活字,都为蒙元时代之物①,敦煌回鹘掌握并开始使用活字印刷的时间,似乎应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75]。第464窟废弃活字之时代,伯希和推定为1300年左右[76]。这些说明该窟在元代时有可能是一个回鹘刊经场所[28]375。在经历数百年之后,在同一窟中尚能发现如此众多的木活字实物,说明当时活字印刷的废弃应是短时间内发生的;反之,如果是逐步废弃的,那么活字实物就会自然散乱,而不可能呈现如此集中的状态。
第464窟前室与甬道壁画为同时所绘,但后室明显与之不同,除了线条、着色迥异外,前室所用晕染法,在后室完全看不到,甬道菩萨造像所用沥粉堆金法,在后室也是看不到的。就绘画风格论,前室所见善财五十三参变与后室所见观音三十二应化现变也迥然有别,前者挥毫恣意,大度有力,潇洒疏朗,颇有大家风范;后者工笔严谨,精致细腻,内涵丰富,呈细密之风[1]23。这些都说明,二者非同一时代所画。前文已论及,后室东壁有梵文六字真言,说明该窟的上限不早于元初。值得注意的是,该窟东壁甬道二侧之画面曾被粉刷过,并覆以回鹘文题记。从壁面的叠压关系,明显可以看出,前室要晚于后室。结合各种因素,可定后室壁画当为元代早期之遗存,其壁画少部分遭到破坏之事,当发生在元朝末期。当时回鹘所覆盖的画面尚相当清新,证明二者时代相距不远,推定为百年以内当不致大误。
这些因素说明,第464窟前室与甬道是回鹘人在蒙古豳王家族的支持下进行修复的,确切地说,具体时间当在元朝末期,但不迟于《吉祥胜乐轮》的抄写年代——1350年。在甬道与前室完工后,回鹘人有意保留了当时保存尚完好的后室,仅对后室东壁甬道二侧的墙壁进行了粉刷,准备题写文字。由于明朝军队突然攻破沙州,文字的题写工作尚未完毕便草草收场了,该窟遂再度废弃。
七 结 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莫高窟第464窟的开凿是在北凉而非目前流行的说法西夏;原为多禅室窟,后来(很有可能为元代)通往南北二壁的禅窟甬道被封堵,多禅室窟变成了毗诃罗窟;由于前室坍塌,原来前室、中室(主室)、后室形制变为前室和后室结构;后来,回鹘在蒙古豳王家族,即沙州西宁王的支持下重修洞窟,并加长了原来通往后室的甬道,构成方室以掩盖方室内侧的元代公主墓,并根据胜光法师译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在甬道南北二壁绘制了十地菩萨像,窟内随处可见回鹘文题记,可确认前室与甬道现存壁画当出自回鹘之手,窟内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六字真言题辞二方,加上洞窟内发现的古代文献、文物绝大多数均属元代末期,故而可确认该窟前室与甬道为元代回鹘窟,更确切地说,应为元末的洞窟。后室则为元代早期洞窟。
与第464窟毗邻的第465窟和第463窟,绘画风格也与其十分近似,故学界通常将以上三窟定为同一或相近时代之物①。那么,第465、463窟是否也如森安孝夫所推想的那样,“是回鹘佛教徒开凿的”②呢?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梁尉英.元代早期显密融汇的艺术——莫高窟第四诸窟的内容和艺术特色[M]//敦煌研究院,江苏美术出版社,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三、九五、一九四窟(元).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11.
[2]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54,62,65.
[3]张大千.莫高窟记[M].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628-629.
[4]照那斯图,杨耐思.八思巴字研究[G]//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74-392.
[5]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J].中国藏学,2003(2):69-79.
[6]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G]//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273-318.
[7]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J].敦煌研究,1998(3):1-4.
[8]关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画装饰风格及其相关的问题[C]//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111-1141.
[9]梁尉英.莫高窟第464窟善财五十三参变[J].敦煌研究,1996(3):43.
[10]王惠民.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及存在的问题[J].西夏研究,2011(1):64.
[11]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J].中国藏学,2002(1):35-37.
[12]刘玉权.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营建年代考论[C]//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130-138.
[13]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73-174.
[14]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J].考古学报,1982(3):377.
[15]索南坚赞.王统记[M].刘立千,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0.
[16]L. de la Vallee Poussin.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M].Oxford University, 1962.
[17]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7,10.
[18]杨富学.浚县大伾山六字真言题刻研究[G]//大伾文化(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83-184.
[19]霍熙亮,编.榆林窟、西千佛洞内容总录[M]//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260.
[20]贺世哲.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与禅观[J].敦煌学辑刊:第1集,1980:43.
[21]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M]//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1:192.
[22]王书庆,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禅窟的历史变迁[G]//中国禅学: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314.
[23]须藤弘敏.禅定比丘图像与敦煌285窟[C]//陈家紫,译.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406.
[24]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343,346.
[25]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2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65.
[26]贺世哲.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12-13.
[27]刘永增.回鹘写本与敦煌莫高窟第二藏经洞[J].敦煌研究,1988(4):40-44.
[28]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M].耿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375.
[29]王三庆.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卷[C]//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79-98.
[30]James Hamilton. On the Dating of the Old Turkish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C]//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Vortr ge der "Annemarie v. Gabain und die Turfanforshung", veranstaltet von der Berlin-Branch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Berlin (9.-12. 12. 1994). Berlin: Adademie Verlag, 1996:135-145.
[31]庄垣内正弘.ウィ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馆藏Or.8212-109について[J].东洋学报:第56卷1期,1974:44-57.
[32]羽田亨.回鹘译本安慧の俱舍论实义疏[G]//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京都:同朋舍,1975:165.
[33]萨仁高娃,杨富学.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J].敦煌研究,2010(1):117-124.
[34]Georg Kara. Petites inscriptions ouigoures de Touen-houang, Gy. Kaldy-nagy (ed.), Hungaro-Turcica[J]. Studies in Honour of Julius Németh, Budapest, 1976:55.
[35]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M]. Oxford, 1972:456.
[36]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M].校仲彝,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418.
[37]Jens Wilkens. Das Buch von der Sündentilgung. Teil 1-2, Edition des alttürkischen K anti k1lγuluq Nom Bitig (=BBT XXV)[M]. Brepols, 2007:68.
[38]中村元.佛教語大辞典[M].東京:東京書籍,1981:1186.
[39]C.Kaya. Uygurca Altun Yaruk Giriγ,Metinve Dizin[M].Ankara,1994:194.
[40]李师政.法门名义集[M]//大正藏:第5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202b.
[41]ジヤツク·ジェス.新出の二大画幅「华严经变相七处九会おょび「华严经十地品变相七处九会にっぃて[G]//尾本圭子,译.ジヤン·フランソヮ·ヤリジヱ,监修,秋山光和,编集.西域美术·ギメ美术馆ペリオ·コレクシヨン(Les Arts de L'Asie Centrale. Collection Pelliot du Musée Guimet:Ⅰ.东京:讲谈社,1994:56-62.
[42]大正藏:第16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419b-c.
[43]F. W. K. Müller. Uigurica[M]. Berli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8:13-14.
[44]S. Ch. Raschmann.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5: Berliner Fragmente des Goldglanz-Sūtras. Teil 1: Vorworte und Erstes bis Drittes Buch[M]. Stuttgart, 2000.
[45]S. Ch. Raschmann.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6: Berliner Fragmente des Goldglanz-Sūtras. Teil 2: Viertes und Fünftes Buch[M]. Stuttgart, 2002.
[46]C. Kaya, Uygurca Altun Yaruk Giri , Metin ve Dizin[M]. Ankara, 1994:194.
[47]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G]//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105.
[48]刘永增.回鹘写本与敦煌莫高窟第二藏经洞[J].敦煌研究,1988(4):44.
[49]森安孝夫.ウィグル語文献[M]//山口瑞凤,编.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74.
[50]Mision Pelliot en Asie Centrale, 1.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Tome 6[M]. Paris: Libairie Paul Geuthner, 1924: 345.
[51]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C]//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24.
[52]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375-402.
[53]宋濂,等.元史:卷60[M].北京:中华书局,1976:1450.
[54]宋濂,等.元史:卷100[M].北京:中华书局,1976:2569.
[55]宋濂,等.元史:卷14[M].北京:中华书局,1976:299.
[56]宋濂,等.元史:卷21[M].北京:中华书局,1976:452.
[57]宋濂,等.元史:卷20[M].北京:中华书局,1976:443.
[58]杉山正明.豳王チュベィとその系谱——元明史料と『ムィッズル-ァンサブの比较を通じて——[J].史林:第65卷第l號,1982:37-38.
[59]宋濂,等.元史:卷108[M].北京:中华书局,1976:2738.
[60]宋濂,等.元史:卷33[M].北京:中华书局,1976:745.
[61]宋濂,等.元史:卷38[M].北京:中华书局,1976:822.
[62]杉山正明.ふたつのチヤガタイ家[M]//小野和子,编.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677-686.
[63]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J].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108-112.
[64]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M]//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84.
[65]段文杰.榆林窟党项蒙古政权时期的壁画艺术[C]//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441.
[66]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247.
[67]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1029.
[68]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敕赐乞台萨里神道碑[M]//大正藏:第4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727c.
[6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2:出伯传[M].北京:中国书店,1984:337.
[70]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J].考古学报,1986(2):253-263.
[71]杨富学.回鹘之佛教[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23-124.
[72]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40,316.
[73]Abuduishid Yakup, Two Alliterative Uighur Poems from Dunhuang[G]//言语学研究:第17/18号.1999: 3-4,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