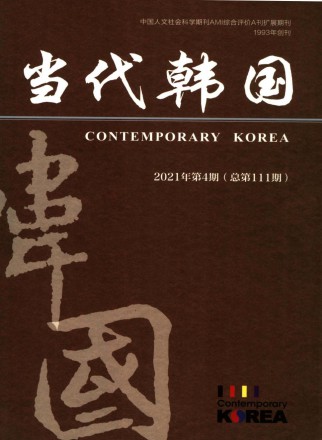汉代的法律形式合集12篇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1
一、秦代的法律制度的全面建立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秦律为基础,参照六国法律,制定了通行全境的法律制度。从睡虎地出土的竹简可以看出,秦代法律大体有四种形式:(1)法律条文。其种类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军爵律》、《置吏律》、《除吏律》等近三十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这些法律是由国家统一颁布的,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成文法。(2)对法律条文的解释。统一之前,秦国行政机构已设立专管法律的官吏,负责向其他官吏和人民咨询法律,并将咨询问答的内容写在一尺六寸长的“符”上。符的左片交给咨询者,右片放在官府封存备查。(3)地方政权的文告。秦政府规定,郡一级政权可以依据朝廷法令制定本地区相应的法令和文件,作为国家法令的一种补充。(4)有关判决程序的规定与证明。这是由朝廷统一的类似后来行政法和诉讼法的有关法令。
秦王朝的法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鲜明的阶级性,维护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专制制度。秦律把商鞅变法以来的土地私有制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凡破坏或侵犯土地私有制和私有财产者,要以“盗贼”论处。秦律还规定:“受田”之民,要按“受田之数”征收赋税,强迫农民交纳田赋。还要按照规定服徭役。不能按期缴纳税赋或服徭役的,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第二,法网严密,条目繁杂。秦律几乎对人民生活的一举一动均作出明文规定,进行严格限制,甚至治罪。“步过六尺者,有罚”,“敢有挟书者,族”,“诽谤者族”,“有敢偶语者,弃市”。甚至连穿鞋都作规定,致使百姓“毋敢履锦履”。这些无端的限制和惩治,形成“赭者塞路,囹圄成市”。 秦统治者认为只有用重刑才能杜绝犯罪。
第三,坚持“缘法而治” 的传统。法令一经公布,包括国君在内,任何人不得更改。《韩非子》中有记载秦昭王不因百姓杀牲为自己生病祈祷而循私情的故事。国君带头执法,故“秦民皆趋令”,秦始皇继承了祖宗的传统,坚持“缘法而治”。二世时期用更加严酷的刑法,带来的后果是秦王朝的迅速灭亡。
二、西汉初期对秦代法律的继承
刘邦入关中时曾“约法三章”,西汉建立以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丞相萧何参考秦代法律,制定了《九章律》,包括“盗、贼、囚、捕、杂、具、兴、厩、户”律。此后的统治者不断地对《九章律》中沿袭下来的秦的苛法加以汰除,如高帝时萧何“除参夷,连坐之罪”,即废除族刑和连坐之法。惠帝四年(前191年)又“除挟书律”。高后元年(前187年)再次重申“除三族罪、妖言令”。文帝元年(前179年)“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下令“除肉刑”,将黥、劓、刖左右趾等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景帝元年(前156年)又将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之后又将笞三百为二百,笞二百为一百,同时还规定,“笞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由于汉初的法制“禁罔疏阔”,所以在惠帝和吕后时期“刑罚用稀”,至文帝时,更是“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虽然汉初“约法省禁”的记载与实际执行的情况有一定距离,但与秦的严刑苛法相比,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刑罚,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汉武帝时期以后法律制度的完备和发展
封建法制的强化和完善西汉建立之初,基于“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在法律上实行“约法省禁”的政策。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客观形势要求统治者必须进一步强化和完善封建法制,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和制定法律的工作。
武帝一改文景时期的宽缓刑法,务求严刑峻法。据史书记载,在张汤和赵禹二人的主修之下,西汉的法律“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西汉中后期的法律制度,大致包括四方面形式:一是律。律是汉代法律的主要形式,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法律形式,晋朝杜预在《律序》中说:“律以正罪名”。除继承汉初《九章律》的内容以外,还制定了《越宫律》、《朝律》、《上计律》、《左官律》、《尚方律》等等。另外,相坐法、沉命法等也属于“律”的范畴。二是令。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竭力宣扬天子受命于天,认为“刑者君之所以罚也”。基于这种理论,皇帝的诏令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封建法律的重要形式了。成文法如与在位皇帝的诏令发生抵触,则以皇帝的诏令为准。汉代“令”的数量相当多,自高祖刘邦制定以来,至成帝时已达一百多万字。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的主要行为规范。三是科。科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另一种法律形式,多是关于人们如何作为的规范,类似于现代的行政法规和民事法规。“科”起源于汉初,“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到汉武帝时,“科”的内容又有增加,“武帝军役数兴,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四是比。又称“决事比”,就是以典型案例作为判决的标准。高祖时即规定,凡廷尉不能决断的案件,应当附上所应比附的律令条文,上奏皇帝。至武帝时,“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由于诸比之间互相矛盾,处罚也轻重不一,以至奸猾之吏借机徇私枉法。
除以上四种法律形式外,汉武帝时还出现一种特别的法律形式,就是“春秋决狱”。所谓“春秋决狱”,就是将《春秋》一书中的“微言大义”作为判断案件的根据。这种决狱标准的出现,是因为汉武帝将儒学作为统治思想,而《春秋》正是儒家经典的《五经》之一。用《春秋》的精神和内容作为审判的依据,这就把儒家的经典当成了法律。其次,由于武帝时制定的法律条文相当繁杂。而用《春秋》中表达得并不十分明确的观念来断狱,便可以抛开繁琐的法律条文和客观事实,根据需要作出各种解释。这样,“春秋决狱”可以给统治者和执法者带来更大的方便,甚至可以不受律令的限制,自然便很快盛行起来。汉武帝曾要求他的儿子学好《公羊春秋》,以便将来作为处理国事的根据。皇帝如此提倡,各级官吏自然就积极奉行起来了。“春秋决狱”这种以儒家思想为审判依据的特殊的法律形式不但对两汉法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且对以后两千年的中国古代封建法制也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2
现代汉语是在古汉语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完善和发展过来的,时至今日,我们可以从现代汉语的世界地位中看到它的独特的魅力,可以从现代汉语的运用中看出它无论是在我们的学习、工作还是生活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现代汉语的研究就显得相当有必要,首先要从它的核心部分---词汇和语法入手,更好的了解它的整个的发展动态。
一、现代汉语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
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语言都有着它特定的表现方式,在清朝晚期向民国过渡的时期出现了一种白话文,在阶段也有着它特定的语言表达方式,现代汉语产生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科技高速发达的时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语言特点。这些都是中国语言宝库里丰富的语言资源,让每个不同的时代对应不同的语言特色,进而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现代汉语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是无处不在的,包括我们的日常交流用语、网络用语、书面用语等等。
日常交流用语中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就是对现代汉语最贴切的运用,现代汉语也让生活在现阶段的我们交流起来更加的简单、顺畅,不会出现古人那种生硬晦涩的语言交流方式,在情感和思维的表达上不仅让表达者表达起来更加的轻松,也让会意者听起来更加的清晰明了。
书面用语是现代汉语最遵循基本表达方式的一种形式,书面用语讲究规范,用词准确,语序恰当,表情达意清晰,真正在词汇和语法上体现现代汉语本质,从书面用语中我们能看到现代汉语结构组成之严格,内容形式之具体。书面汉语运用的场合也很正式,所以对其运用也需要考虑到词汇运用是否恰当,语序位置是否合理。
二、现代汉语本质上的表现形式
现代汉语在本质上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分别为语法和词汇。语言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语言的变化发展在语法和词汇上体现的比较明显,语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语法有着它固定的运用模式,没有语法,语言就形成不了一个完整统一的整体,而词汇则是不断更新变化的,世界变化莫测,词汇就不断更新,事物发展迅速,词汇就不断更迭。
1词汇
词汇是语言的重要构成要素,虽然它是变化发展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相对稳定的规律,词汇就是在这种不断变化和相对稳定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和更新词库的内容。
1.1词汇的内部稳定规律。从词汇的构成上我们可以看出,词汇是由词素构成的,而词素又一般是以单音节语素为主,纵观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我们不难发现,单音节词素占主导地位。
1.2语素构词的语法规律。不同语素之间的组合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最常见的有主谓、动宾、并列三种形式,也是大家最为常见和基本的形式。主谓一般由名词和动词构成,在运用中的使用频率不高。动宾的结构非常广泛的被使用,例如“减肥” 、“炒股”诸如此类的词汇。并列的含义则很清晰,不同的词素具有相同的词性、接近的语义和一定的关联性,比如“茶水” 、“梦想”等等。上述三种结构是最主要的结构,形成了语素构词的基本语法规律。
2.语法
什么是现代汉语的语法呢?语法是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单位的结构规律。语法包括词法和句法两部分。词法主要是指词的构成、变化和分类规律;句法主要是指短语和句子等语法单位的构成和变化规则,包括语结构规则、句法结构规则、句子类型等内容。语法是很抽象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又是语言中的客观存在。只要是语言,就会有一套系统化的语法规律,需要人们按照一定的规律去组织和排列语言,从而让语言更好的成为人们交流和沟通的工具。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2.1现代汉语语法中的词没有形态的变化。
2.2虚词重要而丰富。
2.3句子的语序十分重要。
三、结语
现代汉语是一个与历史相传承与时代相呼应的产物,随着中国近几年来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与世界各国进行的交流更加的广泛和频繁,致使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和地区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从人们对现代汉语浓烈的兴趣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汉语的重要性。本文研究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的发展动态,就是为了人们对学习汉语运用汉语有更规范和更科学的认识。本文也不仅从历史的层面论述了词汇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而且还从从客观的角度研究语法,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入的探讨现代汉语的发展动态,使对现代汉语的研究实现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郑定欧.汉语动词词汇语法.[J].汉语学习.2001年第4期.
[2]刘红妮.非句法结构"算了"的词汇化与语法化.[J].语言科学.2007年第6期.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3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4-0014-02
近十年来,通过与话语分析、语用学、篇章语言学、修辞学、文体学等分支学科的紧密结合,英汉对比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文拟通过对英语物主代词和汉语“人称代词+的”形式进行比较,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规律,并用以指导对外汉语教学中“人称代词+的”语式使用的偏误研究。据考察,目前国内英汉对比研究界,系统阐述英语物主代词和汉语“人称代词+的”形式的相关论文和著作很少。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新颖的研究点。研究点非常具体,讨论的仅仅是英语代词中的物主代词和汉语的“人称代词+的”形式的对比,但是恰好补充了英汉代词对比在这方面的空白。
我们发现,欧美留学生在使用汉语人称代词时常受到英语物主代词的影响。例如,留学生会说:“我戴上我的帽子出去了。”而我们常用的句式是:“我戴上帽子出去了。”这种说法虽然没有语法错误,却并不是常用的形式。这种在语法上没错但在实际运用中不符合常规的现象,我们归结为语用偏误。如例句的英文是:“I put on my cap and went out.”因为母语的影响,留学生组织汉语语句时直接套用英语句式的模式,造成汉语句子偏误。这正好反映了英汉语句式的差异,也是本文提出比较英语物主代词和汉语“人称代词+的”语式的缘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其中有什么对应规律?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有益于对外汉语课堂教学,还能切实解决留学生汉语实际运用的问题。本文将尝试从学习者使用语言的角度出发,从形式、语用、篇章三方面考察英语物主代词和汉语“人称代词+的”语式的不同。
一 造成汉语“人称代词+的”语式使用偏误的省略原因说
有关英语物主代词和汉语“人称代词+的”的差异,虽然还未有专门的研究,但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在论述英汉对比差异时提到过,并普遍认为,这是汉语根据自身的语法特征,依据经济和简略的原则,在话语上的一种省略行为。多数语言学家都提出“人称代词+的”语式省略的说法,认为英语中物主代词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汉语,且在汉语中需要使用“人称代词+的”语式的时候,“人称代词+的”常常被省略。因为汉英语法形式上的差异,汉语不强调语法形式的完整,只强调意义上的表达,因而形式上的东西可以省略;而
英语注重形式上的整齐,各种关系都必须用语言形式表现出来。仅从语法层面比较,汉语“人称代词+的”语式的省略说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但是,省略的说法过于笼统。省略,往往给人一种印象,即本应该有。从汉语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时候是不能加上“人称代词+的”语式的,如果加上“人称代词+的”就错了,在语用上,这是一种偏误。因此省略说似乎不太合适。汉语“人称代词+的”语式有时用,有时不用,中间是有规律的,这正是本文研究关注的内容。
二 本文对“省略说”的看法
省略说认为英语经常使用物主代词,而汉语只是有时候使用“人称代词+的”语式。对于不使用“人称代词+的”语式的情况是因为汉语讲究经济原则,在不影响语义的情况下常常省略“人称代词+的”。例如,“英汉两种语言中代词的使用频率不同,英语中代词的使用频率要远远高于汉语,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汉语中表示所属关系的物主代词往往可以省略,而英语似乎更讲究短语或句子结构的严谨和工整,大量使用物主代词”(梁茂成《英汉代词对比分析及计算机辅助翻译》,1996)。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实际上汉语什么时候使用“人称代词+的”,什么时候不使用,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这主要取决于句子前后的人称是否一致。另外,“人称代词+的”语式的言外之意对其使用也有很大的影响。有些情况下,当英语使用物主代词的时候,相应的汉语不是省略了“人称代词+的”,而是不能使用。例如:
汉语:“我帮你量一下体温。”
英语:“I take your temperature.”
这句话英语使用了物主代词“your temperature”,但汉语中却不能说“我帮你量一下你的体温”。由此可见,这并不是简单的“人称代词+的”的省略。
汉语“人称代词+的”语式的使用不仅和语法有关,有时还和语用有关系。从分析的“人称代词+的”语式言外之意来看,汉语中“人称代词+的”语式有强调和特指两种言外之意,有时为了加强句子的感彩和特定的范围,汉语会特意使用“人称代词+的”。语式例如:
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我和两个妹妹。
我来介绍一下,保罗,这是我的爸爸、妈妈。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4
一、定中标记“之”的相关问题研究
关于“之”字的词性,学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目前影响较大的有介词说、连词说和助词说,其中多数学者则主张助词说,如赵廷琛(1986)、李佐丰(2004)、何乐士(2006)等。
“之”字用法的概述,学者们的看法较为一致。张谊生(2000)在《现代汉语虚词》中认为结构助词“之”带有明显的书面语色彩,主要用于定中短语中,且大都要求定语是双音节而中心语是单音节的。张福酰2002)在《现代汉语虚词500例》中列举了“之”的五种用法,如:用在名词前,表示定语是一种说明;用在主语和谓语之间,使主谓短语变为偏正短语①。《常用文言虚词词典》概括“之”字的功能是用于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标志修饰与被修饰的关系。
基于前人研究,本文认为,将“之”字称为(结构)助词是可信的,并可作为定中短语的定中标记用于定语和中心语之间。
二、方法理论与语料来源
方法理论方面,本文主要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依据韵律构词法、韵律句法的相关理论以及括号悖论理论展开研究。
语料方面,笔者从北京大学CCL语料库检索系统(网络版)中分别抽取了包含“之”字的现代汉语语料和古代汉语语料各1000条。其中,1000条现代现汉语料中,“之”字共出现1805次,充当定中标记的“之”共出现1388次,其后单、双、多音节中心语分别出现1184次、133次和71次,各占比85.3%、9.6%和5.1%。1000条古代汉语语料中,“之”字共出现1949次,充当定中标记的“之”共出现1226次,其后单、双、多音节中心语分别出现928次、262次和36次,各占比75.7%、21.4%和2.9%。
可以发现,助词“之”作为定中标记后跟单音节中心语构成定中短语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下文将对定中标记“之”与单、双、多音节中心语的搭配分别进行论述。
三、定中标记“之”与不同音节数中心语搭配情况
(一)“之”与单音节中心语的搭配
通过对统计语料的分析,“之”与单音节中心语搭配构成的定中短语的数量在“之”字定中短语中占有绝对优势。汉语中大量存在由语义搭配需要构成的普通“之”字定中短语、由定中标记“之”构成的四字成语、“之X”固化结构等等。
“之”字定中短语中存在大量由于语义搭配的需要而组合构成的普通定中短语。例如:
(1)[单音节+单音节]: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羲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周易・乾卦・文言》)
(2)[双音节+单音节]: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尚书・武成》)
(3)[多音节+单音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周易・坤卦・文言》)
“之”字定中短语中较多由定中标记“之”构成的四字成语。例如:
(4)鸿鹄之志 一家之主 养生之道 稀世之宝
媒妁之言 井底之蛙 用武之地 言外之意
定中标记“之”与单音节中心语的搭配,还有很多经过语法化的过程已经固化为“之X”结构,其中“之”与中心语往往结合紧密。例如:
(5)上海农商行排名第213位,已经连续多年跻身全球500家大银行之列;在国内所有入围银行中综合排名第19位。(CCL)
定中标记“之”与单音节中心语的组合还有“之流”“之属”“之辈”“之际”“之间”“之上”“之下”“之中”等。刘云(2010)认为这些“之X”结构都比较稳固,一般具有非扩展性;意义较为凝聚;音节适长,符合人们的词感;使用频率较高。“之X”结构的两个成分“之”和“X”,它们组成了一个标准音步,进而可以成为一个韵律词。从韵律层面来看,“之X”已经形成了一个跨层结构的词。
(二)“之”与双音节中心语的搭配
定中标记“之”后跟双音节中心语的组合,在古代汉语中用例较多而在现代汉语中用例较少。这些双音节中心语,一部分是汉语中固有的双音节词,一部分是[单音节定语+单音节中心语]的组合。
从“之”前后成分的音节数来看,“之”与双音节中心语的组合形式包括:
(6)[单音节+双音节]: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政旧典时式,民之治乱在兹。(《尚书・周书・君牙》)
(7)[双音节+双音节]: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CCL)
(8)[多音节+双音节]:胡敦除了关于设置联络官一点怕暴露其不可告人之企图,因为未予承认外,其余都接受了。(同上)
从“之”后双音节中心语的语法属性来看,中心语也可以是[单音节小定语+单音节小中心语]的组合形式。例如:
(9)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
例(9)中定中短语的中心语,分别是定语“广”“正”“大”与中心语“居”“位”“道”的组合,义为“广大的居所”“正大的位置”“广阔的道路”。我们认为,可以将其分析为由多项定语修饰或限制单音节中心语的定中结构②,即:
“之”与双音节中心语的组配用例较少,而且受到严格的限制:除了一部分古汉语中固有的双音节词,还有上文“A之BC”的临时组合。在此,如果将例(10)a里的“的”换为“之”,则得到例(10)b:
(10)a.北京的春天 万全的计策
浙江的潮水 桌子的上面
b.*北京之春天 *万全之计策
*浙江之潮水 *桌子之上面
由于“之”是带有文言色彩的后附助词,“春天”“计策”“潮水”和“上面”都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双音节词,它们的组合不仅打破了短语的韵律平衡,而且在语体色彩上也有较大差异,所以例(10)b中的定中短语是不成立的。对此,将在下文进行详细的论述。
(三)“之”与多音节中心语的搭配
从统计的语料来看,定中标记“之”后跟多音节中心语的用例极少,合法的组配也受到句法和语用上的严格限制。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
(11)[单音节+多音节]:自文艺复兴以来,众多的思想家们都在高扬与神性相对立的人之自然属性,把人的自然性视为人的本质。(CCL)
(12)[双音节+多音节]:西德之中学教育则以培养德意志文化及为国为民、服务国家之精神为极端。(同上)
(13)[多音节+多音节]:他又在《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一文中,对传统的近代史体系之成就与不足发表看法,提出了“通史总是社会史”的著名见解。(同上)
然而,古汉与现汉的分界过于明显,词汇和语法差异较大,而两者之间过渡阶段所呈现出来的语言特点有时却恰恰能够反映语言中存在的问题。由于本文考察的定中标记“之”无论在古代汉语还是在现代汉语中都可以构成大量的定中短语,因此对“之”的考察就不得不考虑古汉与现汉之间的过渡文体,即冯胜利(2005)在研究汉语书面语法的形式与模式时提出的文言转向白话时“非白不文”的过渡文体,它的特点是“文白掺杂,非文非话”。
关于文白的界限问题,张中行(1995)指出,文言和白话界限不清,主要是文言越界,混入白话。由此来看“之”与多音节中心语的搭配,则主要是由于文言助词“之”越界混入白话而构成的,即定中标记“之”与多音节中心语的组合主要出现在古汉向现汉过渡的“非白不文”的文体中。例如:
(14)近三十年来,古生物学家之发见,亦多有力之证,最著者为爪哇之猿人化石,是石现,而人类系统遂大成。(鲁迅《人之历史》)
四、“之”字定中短语中心语分析的括号悖论
由于“双音节定语+之+单音节中心语”的组合形式是“之”字定中短语的最优组配,因此,我们以这种结构形式为代表来考察“之”字定中短语中心语分析存在的括号悖论情况。
对于“北京之春”等“非标准四字格”形式,尽管按照句法分析这些四字格分析成为“[2+1]+1”,但是一般人的语感都是将“之”字后附在中心语上,即它们的韵律结构都是[2+2]。因此,这些“非标准四字格”可以看作是复合韵律词,符合[2+2]型节律。
除此之外,通过推导,这些四字格形式都符合[轻 中 轻 重]的重音模式。其重音模式的推导,首先需要明确两点前提(冯胜利,2009):a.汉语双音形式的一般重音格式是“轻重”或者“中重”;b.四字格是汉语构词法中的一个构词单位。关于这两点前提,我们只取成说,不做详细论证。我们可以将四字格“北京之春”中的“北京”抽象为双音节形式“AB”,“之春”抽象为双音节形式“CD”。根据前提a,“AB”和“CD”在没有组合之前,其内部的轻重格式分别是A
此时,根据“重音调整原则”,即由两组同等“轻重”成分组成的“轻重”单位必须按“加重重中之重、减轻轻中之轻”的原则进行内部调整。由此可以得到“非标准四字格”的重音模式(设一般情况下的重者为“2”,轻者为“1”):
至此,我们得到了诸如“北京之春”等“非标准四字格”形式的重音模式,即[0 2 1 3](轻 中 轻 重)。这也和标准四字格的重音模式相一致。所以,从以上两点来看,这些四字格形式放弃了句法结构的节律和重音,而改从复合韵律词的节律和重音模式,由此造成了句法与韵律错位的结果,即这些“之”字四音节定中短语的句法结构形式和韵律结构形式之间存在括号悖论。也就是说,定中标记“之”在句法上前附而在韵律上后附。
五、定中标记“之”的韵律效应
(一)关于韵律词的界定
关于“韵律词”的界定,根据McCarthy与Prince的韵律构词理论,冯胜利(1996)认为汉语最基本的音步由两个音节构成,即汉语的“标准韵律词”只能包含两个音节,而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蜕化音步”(单音步)和“超音步”(多音节)才能出现。端木三(2000)认为,汉语普通话的音步是重音在左边的双节拍(双音节)。另外,辅助成分在超词结构中应重于中心成分。王洪君(2000)对韵律词的定义则结合了句法规则与语音规则,认为韵律词是语法上凝固的、节律上稳定的单音步或凝固的复二步,单音步是汉语韵律词决定性的韵律标记。之后,冯胜利(2013)指出,汉语的韵律构词和古来的原生基础词是两套系统;旧词可以单用,但是新词只能成双构造――遵循韵律构词的韵律法则。
此外,冯胜利(1998)对汉语音步的实现方向做了探讨,认为音步的实现可左可右,左向音步是自然音步,右向音步是非自然音步,并分别导致不同的结果,即“右向构词,左向造语”。这不仅回答了音步实现的方向问题,而且还由此引申出了汉语词和语分界的韵律标准。
(二)“之”字定中短语最优组配
“之”字定中短语的最优组配是“之+单音节中心语”形式,因此存在如下对立:
(15)北京之春――*北京之春天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5
1埃及正面律
在古埃及,人们认为法老作为国家的最高首领,受神眷顾,也是太阳神和尼罗河神的化身,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后,都统治着世界,只要肉身不腐,灵魂回归肉体就可复活。因此,古埃及人十分重视尸体的保存,不惜重金制作“木乃伊”和棺材、陵墓,并通过石头雕刻、壁画保存国王、王妃画像。同时,为便于国王在阴间同样享乐,又把人间事物画在墓壁上以供享受。埃及的雕刻、绘画艺术由此产生。古埃及的雕刻、绘画艺术非常独特,具有极其鲜明的艺术特征。
1.1人物造型的特征程式化
与现代绘画不同,古埃及人在进行人物造型时,喜欢着重表现人物最有特征的角度,图坦哈蒙出土的法老金椅上的浮雕和底比斯的壁画就是这种艺术风格的典型。[1]对于古埃及人来说,眼睛从正面看才能够体现人的特征,而人脸从侧面看最为清楚,因此,在画头部时,正面的眼睛和侧面的脸被奇异地组合在了一起;同理,古埃及人觉得人的身体中肩膀和胸膛从正面最好表达,胳膊和腿从侧面看起来更清楚、清晰,于是人的身体就被画成正面的肩膀、胸膛配搭侧面的下半身,特征明确,组合奇异,形成独特的人物造型特点。
1.2总体构图的主观性
由于透视、体量感等现代观察方法的普及,现代绘画的构图多遵循事物的自然面貌。但古埃及人没有这些构图限制,在他们的艺术作品构图中,什么部分重要就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按事物的重要性进行排序。这种构图方式,让画面极具装饰感。当这种方法被应用到壁画中时,更能突出壁画的平面性、稳定性,既可以很好地保持画面统一,又能够清晰地绘制重点局部。古埃及雕刻、绘画艺术的人物特征程式化处理和构图方式的主观性、规范性处理,让古埃及艺术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面貌,让其能很容易地从其他艺术作品中区别开来。有专家将这种遵循严格“规范”和“程式”的图式表达方式做了一个归纳,将其命名为“正面律”:在人物造型中,人脸必呈侧面状态,突出额、鼻、唇,但人眼却是正面而完整的;身体上半身的胸和肩呈正面状态,脚和腿却又是侧面绘制,只要是人物造型,都遵循这种艺术特征,不可随意改动。
2中国古代汉砖造型艺术
在中国古建筑上,存在着一种利用模印制成的砖,或是用雕刻、彩绘方式制作出来的砖,统称为画像砖。最早的画像砖来自战国,在两汉时期盛行于世,一直流传到隋唐,隋唐之后方逐渐衰落。汉朝的画像砖艺术,大致可分为中原(主要为河南)、西南(主要为四川)和江南(主要为江苏)三个区域,其中河南、四川的汉砖艺术最具特色。汉代画像砖表达的主题多种多样,有亭台楼阁,也有花鸟鱼虫,有奇珍异兽,也有神仙传说,有车马出行,也有戏剧舞乐,不一而足,是研究汉代风俗文化、政治经济的重要见证。汉代画像砖人物造型古朴,表现手法简约自然,线条流畅生动,在拙朴大气中透出典雅细腻,具有浓郁的装饰效果。其表现内容取材广泛,构图完整、严谨,疏密有序,满而不塞,杂而不乱,独具美感。“体现在偶像式与情节式的图像组织方式、表达‘所知’、‘所感’的造型思维、流动如生的乐舞精神,这些特色使其艺术形式上充溢着张力,体现出宏大气魄和浑厚雄强的时代精神。”[2]
3埃及“正面律”与中国古代汉砖造型艺术比较
3.1两者同样使用规律性视觉表现语言
龚和德的《戏曲人物造型论》一文中曾讲到,“大凡要求离开生活的自然形态远一点、即加工美化比较多、形式感较强的艺术,都会有某种程式性”。换而言之,具有规律性、概念性、相对稳定的艺术语言表达方式都可以归为“规律性”语言。体现在绘画、雕刻艺术中,就表现为人物造型方式的一致性、构图方式的相似性、艺术手法的类似性上。古埃及壁画、雕刻艺术,其最典型的规律性视觉表现语言,即“正身侧面律”。哪怕经过千年,其人物造型均以侧面的头部、正面的眼睛、正面的肩胸、侧面的腿脚这样的平面造型手法出现,以其极为独特的方式形成极具装饰效果的艺术风格。例如,古埃及壁画《阿门哈特的石碑》(图1),是古埃及中王国第十一王朝(公元前2000年)时期彩色浮雕作品,其中人物的身躯是正面的,而人物头像则是侧面的,人物和景物都被置于一个平面,在一条水平线上进行构图安排,极富装饰性。[3它的另一规律化语言,体现在构图安排上:一般的构图均为横带状构图,人物水平排列,依其重要规定形象大小,极具秩序感。程式化的构图方式突出了绘画的形式感、装饰性。规律性视觉表现语言同样运用在汉画像砖艺术中。在汉画像砖中,规律性视觉表现语言表现在它的造型、构图和表现内容上。所谓规律性的造型,是指在汉代画像砖中,无论是人物,还是车马、鸟兽,造型形态具有整体性,注重外形轮廓,舍弃细枝末节,大气、古拙,比如《戏车图》(图2)。《戏车图》收藏于河南省博物馆,其主要表现的内容是两辆飞马奔驰的戏车,还有几个杂耍的人“,前车杆上伎人两手各握一索,左手握索的另一端由另一伎右手力挽,这位伎人的左手拽着前面的奔马之尾,使绳索成直线状态,两索下有伎人或倒挂或双手抓索作翻滚表演。后车杆上顶部蹲一伎人,与前车舆内之人共抓一索,一伎人做走索表演”,体现出汉时“临迥望之广场,呈角抵之妙戏”的景象。[4]这幅汉砖人物造型简练大气,内部细节概括淡化,是汉砖的典型造型。而规律性的构图,则是指汉代画像砖均为平面二维化构图,人物、动物、景象以侧面和影像为主,构图平整,装饰意味极强。最能体现汉代石砖艺术规律化语言特征的是它的表现内容,在出土的汉砖中,表现车骑出行、神话典故的内容被反反复复使用,而其中的人物形象更是出现在不同的地点,如“荆轲赤秦”等内容到处可见,让人感觉似曾相识。
3.2宗教是两种艺术最常见的表现内容
古埃及壁画、雕刻艺术与古埃及人的世界观有着紧密联系,对于古埃及人来说,每年泛滥的尼罗河让他们感受到了自然的力量;日升日落,星辰运转又让他们认为自然的力量后面有更强大的神,神可以控制自然,超越自然,神可以让人类得到“灵魂永生”,人死后,灵魂不灭,只要肉身不死,人就会复合。因此,所有古埃及的石刻艺术,均围绕着陵墓建筑装饰展开。同样,出现在汉墓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也大多反映出汉人的生死观。汉人认为,人死后是有灵魂的,或成为鬼魂,或成为神仙,这些祖先神灵能够护佑子孙,守护宗族,为更好地祭祀祖先,取悦神灵,守护墓地,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中有不少内容用来表现神仙、神兽。
3.3文化背景造成两者风格特征、表现手法大有不同
毕竟古埃及、古中国相隔万里,虽然其石刻艺术、壁画艺术有一些相通之处,但文化背景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汉代石刻艺术注重整体性,雄浑、大气,讲究“神似”,讲究“意象”,写实性略差而象征性意味浓郁,这与汉代文学、艺术相辅相成;埃及石刻、壁画艺术强调神秘、静穆,人物形态在规律化的语言下更注重结构、比例、动态,写实性更强,色彩更为浓烈,与古埃及当时的审美艺术一致。因为强调外形,讲究雄浑大气,汉代石刻雕琢手法概括、简练;因为注重结构、动态,埃及石刻手法更为细腻、平滑,明显表现出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艺术特征。
4结语
埃及正面律,强调人物造型的特征程式化,注重总体构图的主观性,形式独特,装饰性强,这与汉代石刻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共鸣。汉代石刻艺术,同样注重造型的程式化、规律性,同样具有平面化的装饰性,但与埃及石刻壁画艺术相比,更加简练、粗犷、豪放,更强调造型整体性,更具有写意、象形的意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一致。两者均为人类历史的瑰宝,均值得人们认真揣摩、欣赏、研究。
参考文献:
[1]李于昆.外国美术欣赏[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
[2]刘宗超.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美学特征[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6).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6
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是指通过重叠、加缀等方式或几种方式的综合运用使形容词具有显著描绘性的生动化形式。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符合汉语的节奏规律,因而就有悦耳动听的音乐美,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与它的基础词相比,体现出了非常浓重的感彩。
一、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增强了语句的音乐美
“节奏”是语言的灵魂。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符合汉语的节奏规律,它所显现出来的汉语独特的平仄律等,在优雅的现代汉语主旋律的运用上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因而体现出悦耳动听的音乐美。“语言节奏是指语音的高低、轻重、徐疾、长短及音色的异同在一定时间内有规律地相间交替回环往复成周期性组合的结果。”
平仄可以使句子产生抑扬顿挫的节奏感,读起来才琅琅上口,唐诗宋词之所以能傲视寰宇,历千载而光芒四射,其独特的格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同类型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体现出不同平仄律的音乐美。例如:
①木叶,木叶,木叶
无边木叶萧萧下。(平平仄仄平平仄)(孙玉石《戴望舒》第208页)
②庵前有一潭
微微荡漾(平平仄仄)(王圣思《昨日之歌》第13页)
③是西方的、太行的余脉
有座高山遥遥峙立(平平仄仄)(王圣思《昨日之歌》第12页)
在以上三例中,加着重号的部分一平一仄,平扬仄抑,平悠长仄短促,平和缓仄急剧,平仄相替,形成了参差美,读起来琅琅上口,抑扬顿挫,铿锵有度,韵味和谐,由此也使这些诗句产生了音乐美。
又如:
①来到此地泪盈盈,我是飘泊的孤身,我要与残月同沉。(孙玉石《戴望舒》第9页)
②这里他来了:夜行者!冷清清的街道有沉着的跫音,从黑茫茫的雾,到黑茫茫的雾。(《戴望舒》第214页)
③今天风雨后,闷沉沉的天气,
……
只有你在那杨柳高头依旧亮晶晶地。(胡适《尝试集》第46页)
在以上三例中,加着重号的部分是三音节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它们起到了调节音节,使音韵和谐,节奏鲜明,表达鲜活生动的作用,同时还增强了诗歌的韵味。读起来第一个音节是重音部分,而且稍长,第二、第三个音节读起来不仅轻柔而且短促。“泪、冷、黑、闷、亮、热、乱、阴、活、莽、白”的声音好像是沉稳浑厚的定音鼓,而词缀“盈盈、清清、茫茫、沉沉、晶晶、滚滚、纷纷、苍苍”等,好比清脆悦耳的沙锤铃。二者搭配协调,节奏明快,好似一曲曲美妙、悦耳、动听的华尔兹乐章。将它们运用到文学作品中去,与其它诸多单音节词、双音节词等互相配合,互相协调,就为丰富作品的音节,增强作品的节奏感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使文章读起来节奏鲜明、抑扬顿挫、富有节奏强烈的音乐性,可以大大增强文学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二、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增强了语句的感彩
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与它的基础词相比,体现出了非常浓重的感彩,褒贬之义有所增强,这种感彩有的是体现欢乐、喜爱、亲切、亲热、等的意味,有的却体现出痛苦、厌恶、反感等的意味。
1.体现欢乐、喜爱、亲切或中性的感彩
1.1有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用在定语和谓语的位置上往往表现出欢乐、喜爱、亲切等的意味或中性的感彩。例如:
①顷刻间把进来的两个人团团围住,有的抢上去握手,有的抱着他们的膀子,眼里流着涔涔的热泪,……(魏巍《东方》第5部第13章第958页)(“涔涔”作定语)
②她的声音潮潮的,在电话里,阴天似天。(万方《空镜子》第122页)(“潮潮”作谓语)
③大家都衣冠楚楚,脸上的表情很严肃,绷着劲,故意不交头接耳,碰到熟人只点点头,又一种文明且神秘的气息。(万方《空镜子》第123页)(“楚楚”作谓语)
“楚楚”有喜爱、亲切的意味,具有[+褒义]的语义特征,而“涔涔”、“潮潮”却具有[+中性]的语义的特征。
1.2儿化之后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则往往带有惹人喜爱、欢快的意味。例如:
①表嫂家的孩子,特别可爱,长得圆得乎儿的。
②红玉苹果酸不叽儿的挺好吃。(转引自《现代汉语八百词》第639页)
③儿子考上了省重点,老王心里美滋滋儿的。
以上例句中加着重号的部分体现了喜爱或欢快的内心感受。
1.3带有“洋洋”、“晶晶”、“扑扑”、“丝丝”、“茸茸”、“滋滋”、“悠悠”、“墩墩”等词缀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也具有让人欢乐、喜爱的意味。例如:
①田九麦的病老娘此刻也不病了,喜滋滋的吃着各家送来的吃食。(《小说月报2005年精品集》第68页)
②我心里甜丝丝的,心想这个同志不光对人好,懂得的道理也多。(马忆湘《朝阳花》第14章第252页)
③娇娇扬着粉扑扑的小脸蛋,踮起脚尖,安慰着受伤的小鹿。
2.体现痛苦、厌恶、反感的感彩
与具有贬义感彩相关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像“黑压压”、“毒花花”、“臭乎乎”、“臊烘烘”、“灰溜溜”、“恶狠狠”、“乱糟糟”、“酸不叽”、“冷不丁”、“黑不溜秋”、“圆得噜”、“土头土脑”之类,都具有令人反感、厌恶的感彩。例如:
①机关副处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足有好几十人,黑压压地挤满了会议室。(《小说月报2005年精品集》第225页)
②我也不准能在外面混出个模样来,……,我要是灰溜溜地回来了,你爹也不能同意你嫁我。(《小说月报2005年精品集》第69页)
③终于,埋着头等待的表姐抬起头来,恶狠狠地瞪着我:“……?”(《小说月报2005年精品集》第375页)
以上三例中加着重号的部分体现了一种贬义的感彩,亦或厌恶,亦或反感。
参考文献
[1]哈森.现代汉语[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
[2]吴洁敏.论汉语节奏规律[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3]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4]赵惠.现代汉语形容词生动形式[D] .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年.
[5]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6]哈森.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形容词生动形式[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7
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词汇为建筑材料、语法为结构规范的一种符号系统。其中,词汇是最敏感、最活跃、涵义最丰富的部分,也是最能反映民族文化特点的部分。汉语的词汇系统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与时俱进,从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到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汉语词汇的双音化现象早已引起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列式双音词作为较为能产的一类词汇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深入探讨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机制对整个汉语史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比其他语言,都没有一个成系统、数量如此庞大的并列式双音词体系,因此,深入研究并列式双音词对于汉语构词法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语言内部机制
(一)韵律机制的影响
1.韵律的制约
冯胜利先生提出韵律词概念,是从韵律学的角度来规定“词”的概念。根据冯先生的论断,韵律构词学的理论基础——“韵律层级”,从上到下依次为:韵律词——音步——音节——韵素,即韵素组成音节,音节组成音步,音步实现韵律词,而音步必须同时支配两个成分,即“二分枝音步”,因为没有二分,就没有“轻重抑扬”,也就构不成韵律。
据学者统计,从上古时期东汉开始,双音词就已经出现并成为词汇的一种发展趋势,到中古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并列式双音词。这里所说的并列式双音词是指由两个单音节词根语素并列构成的双音节词,按其两个语素之间的语义关系,学界把并列式双音词分为同义并列、反义并列和类义并列三种类型。李仕春在《联合式构词法在中古时期最能产的原因》一文中论证了“并列式构词法在中古最能产(见图1)。到了现代汉语中,并列式双音词仍是仅次于偏正式的第二大词汇群,纵观古今语音系统的变化,可以得到一些线索。冯胜利在《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一书中提到,上古到中古汉语的语音演变特征可以描述为“在新韵律系统里,最小的韵律单位(音步)不是单音节,而是双音节”,这一结论的得出充分证明了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音节结构的演变就是双韵素音步到双音节音步的演变,即“双音化”的历史来源。
图1 中古时期偏正式和联合式复合词使用情况
到了现代汉语,双音词占明显优势,根据冯胜利先生的韵律理论,汉语在双音步的制约下,越来越多的短语逐步固化为韵律词;为了满足韵律的要求,本可由一个单音词表达的意义,改由两个相同意义或相近意义的单音词连用表达,促使大量的同义并列双音词产生。
发端于魏晋的,兴盛于南北朝的骈文是汉语文学史中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的时期。骈偶与对仗这两种重要的修辞手段被看做汉语韵律构词系统的必然产物,但过分追求对偶,就走入了一个“文必四六”的极端。文学上的这种风气其实就是对双音步的偏爱,导致了大量双音词的产生,之后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批判过分追求辞藻华丽的骈文之风,推崇单音单语,一些完全出于对仗考虑,没有实际意义的双音词慢慢淡出词汇系统。但词汇的双音化仍然成为一种不可改变的趋势。
2.语音系统的变化
词是音义结合而产生的,而音义结合是任意的,《荀子·正名》:“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这并不等于音义之间毫无联系,沈兼士《声训论》:“凡意之寓于音,其始也约定俗成,率由自然。继而声义相依,展转孳乳,先天后天,交错参互,殊未可一概而论。”说明语音对词汇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据王力先生统计,上古汉语的声母32个,韵母29个,声调有4个;中古汉语的声母35个,韵母92个,声调也有4个,语音明显比上古复杂得多,尤其是清唇音、舌上音的产生及庄、章二组的合并、大量古入声字的语音变化对词汇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的记忆负担加重,而中古时期政治、文化繁荣发展,新事物不断产生,对于新词语的需求也不断扩大,音节的数量的有限性决定了大量同音字产生,对言语交际带来了不便,音变造词法已经不适应当时的交际要求。
3.方音影响
伴随着隋唐盛世的出现,各地人们交往频繁,商业往来密切,方言的流通度大大增强,不同方言中表达同样意义的单音词在交际中引起不便,逐渐发展为同义词、等义词,这些词语有的和当时的共同语结合,有的方言单音词汇则互相结合,在词汇“双音化”的过程中逐渐合并。如《方言》卷一:“晋魏河内之北谓惏曰残,楚谓之贪。”《说文》:“河内之北谓贪曰惏。”(注:“惏”即“婪”),“贪”、“婪”二字表示同样的意义,只是方言的不同,因而在交际中逐渐合并为“贪婪”这一并列式双音词。
(二)联合式句法的影响
汉语构词法从词的内容上考察时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使用词根原形,第二类是改变词根部分的语音,即改变音素或声调。具体分为摹声法、拟义法和变义法。从词的形式上考察的有音变构词法。在以单音词占主导地位的上古汉语中,摹声法毕竟可取范围有限,而拟义法造词,词语的义项过多,在交际中容易混淆,有时也难以分辨义项与义项之间的分界,如“墨”,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仅名词义就有“书画作品”、“黑色”、“墨线”、“长度单位”等八个义项。变义法和音变法造成的结果是大量单音同音词的产生,在文字上的影响是大量假借字、通假字的产生,给交际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汉语是缺乏严格意义形态变化的语言,即“孤立语”,以单音节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汉语的这一特点在上古汉语中就表现为一字、一词、一音节的对应现象,为联合式构词法的产生提供了大量的构词素材。人们在表达时根据表达的需要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些已有的单音词,把语法、语义上能够搭配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音词连用,这样就形成了联合式的短语或句子,有些久而久之就固化成了一个词。这是一些双音词在词典里具有双重身份的原因,既可以是词,又可以是习语,带有短语的特征。这类词介于自由短语和词汇之间,是词汇化的对象。
(三)训诂的影响
战国末年就已经出现了注解古籍的专著。训诂学的萌芽在春秋末年就已经开始。春秋以后,孟子提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是训诂学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何为训诂呢?如“勤,劳也;遵,循也。”(《逸周书·谥法解》)“论:议也。”(《说文解字》)“追,逐也。”(《说文解字》),通过因形求义、因声求义、因文求义等方法训释词义,又利用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单音词形成互训、同训、递训等解说词义的方法。与此同时形成了大量的同义、类义的单音词构词素材,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这些经常高频同时出现的单音词逐渐凝固为并列式双音词。另有由反知正的训释方法,如“浅,不深也。”(《说文·水部》)曾字足义的训释方法,如《诗经·小雅·六月》:“比物四骊,闲之维则。”毛传:“则,法也。”疏云:“维有法则矣。”毛亨用单音词“法”来训释,孔颖达则改用了复音词“法则”,可见训诂对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语言外部机制
(一)汉民族传统文化影响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讲求一个“和”字,直至当今社会仍然倡导“和谐社会”,汉民族传统的哲学观和审美观讲求对称、追求形式美,这些在汉民族传统文化中都有体现。如我国的民间传统艺术剪纸,多是体现了对称美;在汉字的字形中不乏对称的现象,如“喜”、“山”、“天”等;更有“成双成对”、“好事成双”之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春节,“贴春联”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对称、和谐的追求,并在其中予以了浓浓的祝福、祈愿之情。这样的传统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上,如上文提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一时的骈文,就是对这种对称的形式追求到极致的表现。在词汇上的体现并不少见,人们往往纯粹是为了达到某种表达效果而故意做出有意识的双音选择,因而有了“足辞”之说。马建忠先生指出:“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辞气稍觉浑厚耳。”此语道出了并列式双音词在表达效果上的作用,即加强语气。如并列式双音词中有一类特殊的词语,叫做“偏义复词”,在这类词中只有一个语素有实际意义,而另一个只起陪衬作用,如“国家”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只表“国”,不表“家”;“窗户”只表“窗”不表“户”,“妻子”只表“妻”不表“子”,这样的一类词在现代汉语中并不少见。
(二)认知机制影响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在面对事物的多样性时,人类认识新事物时总是以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通过类比的方式将未知事物与已知事物联系起来,从而扩大自己的认知域。大脑对世界的认识不能是杂乱的,而应采取分析、判断、归类的方法,将其进行分类和定位,将客观世界范畴化。汉民族独特的认知机制连同客观世界的需要导致了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认知语言学认为,大脑的经验范畴与自然界的范畴最接近、最匹配,是认知的重要基点和参照点。如“风雨”一词,“风”和“雨”分别表示自然界的两种常见的、具体的自然现象,人们在交际表达时,把这两个词连用,用来描述天气状况,多用于描述天气恶劣。人们根据联想和感知,用“风雨”一词比喻危难和恶劣的处境或人生的坎坷之路,这就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映射。认知机制在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尤其是其比喻义的产生方面具有重要影响。
三、结语
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理据既有语言的内部的又有语言外部的,无论是韵律、语音、构词法、训诂学还是传统文化和认知机制都对并列式双音词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的分析还不尽全面,尤其是在语言外部机制上的研究还略显单薄,笔者会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完善。
参考文献:
[1]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M].商务印书馆,2005.
[4]孙常叙.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概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5]万献初.现代汉语并列式双音词的优化构成[J].汉语学习,2004(2).
[6]张博.先秦并列式连用词序的制约机制[J].语言研究,1996(12).
[7]李仕春.联合式构词法在中古时期最能产的原因[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7).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8
一.律、律学
“律”,是一个很古老的字,甲骨文中有之,《易经》和《尚书》中亦有之。《说文解字》曰:“律,均布也。”按前人的解释,“均”是一种木制的工具,长八尺,上面有弦,用以调声。“布”是分布之义。用“均”将十二种音调和谐地分布在乐器上,即为“均布”。从古人对“律”的释义中可以看出,“律”的本义为音律。古乐中有以六律较五声(宫、商、角、徵、羽)之说。以律较声,律由是得出“范天下之不而归于一”的引申义。律在师旅中又引申为纪律、约束之意(如《周易》中就有“师出以律”的说法),这一用法在先秦的军队中已得到广泛使用。从公元前356年起,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他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2,制定了秦律,“律”即成为当时及后世绝大多数王朝最主要的基本法律形式。
中国古代律学(亦称“刑名之学”、“刑学”)以注释法学为主体,它主要研究以成文法典为代表的法律的编纂、解释及其相关理论。作为一种以古代法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形态,律学关注的视角既包括立法原则的确定、法典的编纂,也包括法理的探讨、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等。秦汉以来,律学研究名家辈出,成果斐然,不仅出现了如郑玄、张斐、杜预等一大批杰出的律学家,而且产生了以《律注表》、《唐律疏议》为代表的诸多律学经典著作。可以说,律学的发展对于中华法系的确立与发展、对于古代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法制建构都给予了重要而有益的理论支撑。
二.中国古代律学的阶段分野及其成就
1.律学在先秦的初萌
先秦时期律学研究的萌芽,有着多方面的历史表征。早在西周初期,刑法原则中就有了针对犯罪主观心理状态如眚[过失]与非眚[故意]、终[惯犯]与非终[偶犯]的明确区分,诉讼程序上也出现了狱[刑事]、讼[民事]之别,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从理论的高度探讨法的现象与其适用的问题。春秋时齐国的管仲曾从概念上对法的含义予以阐释,他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公元前501年郑国大夫邓析作《竹刑》,虽然该书内容已不可考,但从当时的执政者将其作为成文法加以应用来看,《竹刑》当属萌芽期的律学著作,邓析本人也被后世奉为古代“讼师”及律学研究的鼻祖。战国初年魏相李悝在变法中主持撰成《法经》一书。虽然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成文法典,但就编撰体例、篇章结构和实体内容来看,《法经》不愧为初萌期律学的最高成就,它在律学乃至中国古代整个法律文化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法经》首次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宗旨和“重刑轻罪”的重刑主义原则,初步创立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篇章体例结构,为封建律典法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对后代王朝的封建立法及其法制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先秦时期初萌律学的发展还很稚嫩,这种探索性研究其本身还处于偶然和自发的状态,其初衷甚至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和一味用刑的法家偏激主义倾向;然而它却为律学在秦汉时期的发轫乃至于后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背景,作了十分必要而有益的准备。
2.秦汉时期——律学的发轫阶段
律学在秦汉时期的诞生,以秦代法律注释书《法律答问》等的出现、西汉和东汉相继展开的以经释律、以经注律活动等为主要标志。律学在这一时期滥觞,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首先,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以及国家的制度设计的日益完备等,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其次,这一时期成文立法的发达、立法活动的频繁以及法律数量的日益庞杂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客观的需要。再次,秦汉时期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经学的发达以及语言学、文字学和逻辑学的进步为以法律注释活动为主要表征的秦汉律学研究的展开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环境。
作为以法家理论治国的典型,秦王朝虽然由于其高压的集权统治而对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活动均予以取缔和镇压,但却异常重视法制,实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国策,从而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国家支持(以《法律答问》为代表的法律注释书的风行即是很好的例证)。尽管秦代律学由于缺少其他的学术支撑而在表现形式上仍略显稚嫩,但它却为两汉时期律学的持续的开创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朝建立后,经过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两汉的统治者逐渐认同并采用了“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治国方针,通过说经解律、引礼入法以及推行春秋决狱等,把封建法制与儒家伦理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开始了封建伦理法制化、封建法制道德化的进程。因应这种时代的政治背景,两汉时期的律学研究也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突出表现为董仲舒等儒家经学大师的以经释律及东汉学者将经学方法应用于律学研究并进行的以经注律的实践。如果说西汉的律学研究因为克服了一味用刑的缺陷而培植了较为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东汉时期通过训诂方法(经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律学研究则变得更为系统、周密和严谨。据《晋书-刑法志》载:对当时(汉)的律文“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东汉学者的律章句,是东汉时期最典型的律学著作,为秦汉时期律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儒者们通过律章句对汉律令中的概念、立法背景和历史渊源等均作出了各自比较精确的界定和阐述。
比照初萌期的律学,秦汉诞生期的律学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它内容更加丰富,注释也更为详尽。秦汉律学有对某项法律、法令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演变的阐述分析,有对律文的立法宗旨、含义的归纳总结,还有对法律概念、术语的训诂、解读和界定,呈现出一种较为系统的状态。其次,律学研究中儒法合流的趋势明显。秦代律学对宗法伦理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如秦律规定:“父盗子,不为盗。”而两汉时期法制的儒家化更使律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儒家的思维与视角所同化。汉时的儒者不仅用儒家经义来阐述法律文意,而且用经学方法来诠释法律概念。再次,秦汉律学开创了立法与编撰律疏同时(如秦朝的《法律答问》)、法律注释与私学并行和前文已述的以经释律等传统,这些都对后世影响极大。
3.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
尽管律学于秦汉时期诞生,但对律学研究予以明确记述并使用“律学”来指称法律注释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却是魏晋以后的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性演变时期,秦汉早期的封建法制经由它完成了向成熟完备的隋唐封建法制的转变。在长达近四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封建集权统治的相对削弱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整个社会的结构(包括文化结构)在剧烈的变动中得到了新的整合。因应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独立性明显增强并呈现较前代更为昌盛与活跃的形态。主要表现在:
〈1〉儒家思想在律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律学研究儒家化基本完成。可以说,律学的诞生过程,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律学研究儒家化趋势日益发展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在国家立法、司法活动中,在社会的律学研究中的影响,不仅较秦汉更加广泛、深入,而且出现了系统化、制度化的倾向,为隋唐及后世律典的“一准乎礼”奠定了基础。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这一时期“十恶”、“八议”等的出现以及围绕“十恶”、“八议”的入律,律学家们从经义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的深入研究和阐述。
〈2〉律博士的设置和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的形成。
公元227年,卫觊上奏魏明帝:“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魏明帝采纳了卫觊的建言,于是曹魏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9年)颁布《新律》的同时,在廷尉之下,置律博士一人,位第六品中中,负责对地方行政官吏和狱吏教授国家的法律、法令。此后西晋及南北朝时期的政权也大都设有律博士或类似职位。魏晋南北朝的律(学)博士,是在司法机构廷尉或大理寺之下的属官。这样,法学教育附属于司法行政之下,律博士们既研究、教授法律,也参与立法与执法活动。又据史书载,后秦姚兴当政时期(394-416)于长安设立律学,“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设立的第一个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律博士和独立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的设置,使律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偶然自发的状态和单纯的学者热情而具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对促进这一时期律学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名家辈出与律学地位的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名家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职业阶层。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曹魏时期的刘劭、卫觊,西晋时期的杜预、刘颂、张斐,南北朝时期的封氏家族等。律学家们或直接参与当朝立法,或对成文法典的条出权威性的注解——这些注疏经由官方认可甚至可以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文件,从而使律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律学研究在国家法制建构中的作用也日益彰显。例如律学家杜预曾直接参与《晋律》20篇的制定工作,而由封述(出身渤海律学世家封氏家族)主持完成的《北齐律》则取得了这一时期立法的最高成就。又据《晋书-刑法志》载,太和初年,魏明帝下诏要求各级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但用郑氏[注:指郑玄]章句[以经释律著作],不得杂用余家”,这一规定使私人对法律的注释在历史上首次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司法文件。当然,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律疏注释成果当属张斐、杜预两位律学家对《晋律》所作的注本和律解。他们的晋律注经晋武帝诏颁天下,具有了与法典律文条目相同的法律效力,以致后世径称《晋律》为“张、杜律”。
〈4〉方法论的进步和律学研究的深入与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晋代以后,由于玄学宇宙观和“辨名析理”方法论的影响,律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了进步。律学家们一般不再单纯使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条文和法律名词,而是更多地使用抽象的逻辑思维及归纳、演绎的推理方法,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趋势愈加明显。
在方法论进步、法制发展、文化昌明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律学在研究上愈加深入繁荣,其成果集中表现于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改革与创新之中。其一是魏晋律的制定和刑名法例篇的定型;其二是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于世的并为隋唐律典十二篇目、五百条文的结构体系提供了直接历史渊源的《北齐律》的制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除了上述四点表征,还表现为刑法原则的确立与完善、法律解释的精确与明晰等等,笔者限于篇幅,此不赘言。虽然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有着浓厚的承启性色彩,然而毋庸置疑,其在整个律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重要而关键的,而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革新法制方面的独特的开创性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律学史、法制史中无疑将永放光芒。
4.成熟与发达的隋唐律学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封建法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空前的完备状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因应立法发展、法学教育全面展开、法学世界观进一步成熟的时代法制背景,在总结吸收前代律学成果的基础上,律学在隋唐时期步入了历史性的成熟与发达阶段。主要表现在:
1)官方及私家编纂的律学著作为数众多(代表性著作为唐长孙无忌等人奉诏编著的《永徽律疏》)且社会普及度较高;
2)以儒家为核心并综合各家精华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全面渗入到律学的研究之中3;;
3)律学研究中有关法律体系的理论进一步成熟,体现立法学成果的法典的结构也更为合理;
4)刑法的基本原则更为丰富,刑罚的体系更加完善;
5)专门性法律制度的研究更为深入;
6)律文注释更为全面(如在阐述“十恶加重”原则时,唐律疏议对“十恶”重罪的立法意图和宗旨均作了详尽的说明和论证,并阐释了与之相关的皇权原则、宗法伦理原则及贵贱尊卑等级原则等),法律名词概念的解释更为精密周全(如唐律疏议在探讨“罪刑法定”问题时虽然指出:“事有时宜,故人断制敕,量情处分”,但同时也认为人主之断为个案,强调“不得引为后比”);
7)律学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
隋唐律学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巅峰时刻”,而作为中华法系的标志性律典和人类历史上三部最杰出的法典之一的《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则是这一时期律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从唐律的结构体系看,作为中国古代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其序列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它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犯罪居中,诉讼程序置后”,整部法典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充分体现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创新。前人有言,唐律“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范围甚详,节目甚简”。的确,唐律不愧为我国古代法学世界观和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继承了历代立法的成果,其本身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从而达致了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为唐代封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在后世中国及东亚、东南亚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当社会稳定发展、成文立法发达,讲求“法条之所谓”的律学便会兴旺。隋唐律学的成熟与发达,尽管有其历史积淀的因素,但也正是上述规律的具体体现。当然,律学在隋唐时期的成熟与发达已经有着浓厚的总结性色彩,而其在唐之后的衰微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物极必衰”的哲理——然而这却并不构成我们置疑隋唐律学之辉煌成就及其历史性地位的理由。
5.走向衰微——宋元时期的律学研究
唐朝灭亡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由动荡的五代十国进入到了地区局势相对稳定的宋辽夏金元时期,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多元法制并存阶段(其中宋元法制较为完整)。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较之隋唐,其形衰式微的趋势明显。然而独特的社会时代背景赋予宋元时期律学以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其时斑斓的封建后期法制的建构。
终两宋之世,律学兴废几番,其路坎坷。律学教育在宋朝有三次大规模的兴起,即所谓的“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及“崇宁兴学”,这三次“兴学”可以认为是两宋读书读律风行及律学研究较为活跃的时期。然而,尽管宋朝统治者对当时的读律之风予以了肯定,但其在设置律博士和官方法律教育机构“律学”问题上的游离不定的态度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律学的发展4。再加上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日益确定、两宋时期对总结司法审判经验的异常重视以及宋代司法中敕的风行等等使得律学在两宋时期事实上沦为“小道”。然而即便“落寞”如斯,两宋律学依然在历史上绽放出了其独特的光彩,突出表现在有宋朝特色的立法成果《宋刑统》之中。《宋刑统》由宋太祖时期的朝廷司法官员和法律专家受诏编撰,经由太祖皇帝诏颁天下而成为两宋通行全国的刑书类型的根本大法,其独特之处在于:1.采用刑律统类的形式,不仅是中唐以来立法编撰形式的一次重要变化,而且也是对传统的封建律典命名的革新。2.添附敕令格式的体例,首开我国立法史上律令敕式合编体例的先河。《宋刑统》不仅在两宋时期得到实施,它还影响到了辽、金、元至明清时期甚至于东南亚诸国的立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朝律学研究的独特的富有开创性的成就。
元朝未设律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时律学研究的偃旗息鼓。作为我国古代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进行统治的大一统的封建政权,元代的法制有着浓厚的夷族色彩(如确认各民族间的不平等地位、维护落后的生产方式、保留蒙古习俗、赋予宗教僧侣法律特权等等),但其主要的趋势是汉化、封建化。元朝的立法,从1291年的《至元新格》、仁宗时期的《风宪宏纲》到1323年的《大元通制》、1346年的《至正新格》,有元一代的法典编撰“附会汉法”,到处可见律学的影子(应用了汉人历代政权的律学研究成果)。虽然元代律学无法同隋唐甚至两宋的律学研究相比拟,但我们必须看到其在夷法汉化、封建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的历史作用,而其凭借元朝强大的军政帝国实力所达致的周边影响力也同样不可轻视。
6.律学在明清时期的历史性终结
处于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晚期的明清二朝,其封建法制在隋唐宋元的基础上在封建专制集权统治极端强化的背景下又有所发展,法制因应集权专制的需要而更加严酷,司法也愈加腐朽。在这种条件下,我国古代律学也终于在僵化的总结与思考中失去了生命力,在登峰造极的因袭与保守中走向了历史的终结。当然,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明清时期我国古代律学对邻国较之前代毫不逊色甚至更为突出的影响。
有明一代,立法活动主要集中于开国之初。从历30年编纂始成的以“严”、“简”著称的《大明律》,到堪称古代中国社会普及度最高的封建法典的明《大诰》以及各种例典,无不是在明初统治者尤其朱元璋的重典治国立法思想的指导下完成的。作为明代法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刑用重典”表征着汉唐以来在立法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此成为明代律学的一大特色(虽然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朝统治者的意志)。尽管律学在明代总体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与僵化,但明代律学著作的极大丰富与较为完好的保存、其时中国律学对满清一朝及周边诸国尤其日本、朝鲜和越南法制建构的突出的影响力,却使其在整个中国古代律学史中占有了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
与明朝相比,满清时期的律学异中有同。一方面,少数民族的背景使其法制建构凸现民族特色,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也有带上了浓厚的民族融合的色彩;另一方面,因袭明制并走向终极的专制主义集权政治对这一时期的律学发展同样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虽然清朝的私家注律盛极一时,但出新的很少,绝大部分是在整理“祖宗的家底”。当然,这种整理旧故本身也是清代律学较为活跃的体现,而且也确实出了一些成果,比如薛允升的《唐明律合编》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比较法著作。另外,清代律学对周边国家的法制也同样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不管怎么说,鸦片战争渐渐的近了,西学东渐的思潮即将涌动,我们的古代律学也将在隆隆的近代化的号角声中走向终结。而清末律学家沈家本因应时代而进行的中西结合的律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我国古代的律学研究画上了一个兼具传统底蕴的近代化的句号。
尾论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9
一.律、律学------------------------------------------2
二.中国古代律学的阶段分野及其成就---------2
1.律学在先秦的初萌--------------------------------2
2.秦汉时期——律学的发轫阶段-----------------3
3.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4
4.成熟与发达的隋唐律学--------------------------5
5.走向衰微——宋元时期的律学研究-----------6
6.律学在明清时期的的历史性终结--------------7
尾论---------------------------------------------------- 7
内容摘要:律学在中国古代法制建构与完善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扩充了法的内容,解决了由于成文法条的抽象性、具体案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带来的诸多法律适用问题。从先秦到明清,古代律学因应时代,一脉相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国古代法制进程的推进提供了持久稳定的动力,为中华法系的形成和整个东(南)亚古代社会的发展演进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法理支持。其斐然的成就、独特的法学视角和学术文化系统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学研究乃至于国家法治的最终实现都有着特殊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律学 律学成就 阶段分野 再认知 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引 论
法学论域内的律学,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领域,也是中华法系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中国古代法学中的至显之学,律学萌芽于先秦,滥觞于秦汉,独立于魏晋,成熟于隋唐,衰微于宋元,终结于明清1 。本文拟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对古代律学的发展及其成就予以概括性的阐述和再认知。
一.律、律学
“律”,是一个很古老的字,甲骨文中有之,《易经》和《尚书》中亦有之。《说文解字》曰:“律,均布也。”按前人的解释,“均”是一种木制的工具,长八尺,上面有弦,用以调声。“布”是分布之义。用“均”将十二种音调和谐地分布在乐器上,即为“均布” 。从古人对“律”的释义中可以看出,“律”的本义为音律。古乐中有以六律较五声(宫、商、角、徵、羽)之说。以律较声,律由是得出“范天下之不而归于一”的引申义 。律在师旅中又引申为纪律、约束之意(如《周易》中就有“师出以律”的说法),这一用法在先秦的军队中已得到广泛使用。从公元前356年起,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他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2,制定了秦律 ,“律”即成为当时及后世绝大多数王朝最主要的基本法律形式。
中国古代律学(亦称“刑名之学”、“刑学”)以注释法学为主体,它主要研究以成文法典为代表的法律的编纂、解释及其相关理论。作为一种以古代法律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形态,律学关注的视角既包括立法原则的确定、法典的编纂,也包括法理的探讨、法律的解释与适用等。秦汉以来,律学研究名家辈出,成果斐然,不仅出现了如郑玄、张斐、杜预等一大批杰出的律学家,而且产生了以《律注表》、《唐律疏议》为代表的诸多律学经典著作。可以说,律学的发展对于中华法系的确立与发展、对于古代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法制建构都给予了重要而有益的理论支撑。
二.中国古代律学的阶段分野及其成就
1.律学在先秦的初萌
先秦时期律学研究的萌芽,有着多方面的历史表征。早在西周初期,刑法原则中就有了针对犯罪主观心理状态如眚[过失]与非眚[故意]、终[惯犯]与非终[偶犯]的明确区分,诉讼程序上也出现了狱[刑事]、讼[民事]之别,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从理论的高度探讨法的现象与其适用的问题。春秋时齐国的管仲曾从概念上对法的含义予以阐释,他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 公元前501年郑国大夫邓析作《竹刑》,虽然该书内容已不可考,但从当时的执政者将其作为成文法加以应用来看,《竹刑》当属萌芽期的律学著作,邓析本人也被后世奉为古代“讼师”及律学研究的鼻祖。战国初年魏相李悝在变法中主持撰成《法经》一书。虽然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成文法典,但就编撰体例、篇章结构和实体内容来看,《法经》不愧为初萌期律学的最高成就,它在律学乃至中国古代整个法律文化史上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法经》首次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宗旨和“重刑轻罪”的重刑主义原则,初步创立了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篇章体例结构,为封建律典法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对后代王朝的封建立法及其法制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先秦时期初萌律学的发展还很稚嫩,这种探索性研究其本身还处于偶然和自发的状态,其初衷甚至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功利性和一味用刑的法家偏激主义倾向;然而它却为律学在秦汉时期的发轫乃至于后世的长足发展提供了适宜的背景,作了十分必要而有益的准备。
2.秦汉时期——律学的发轫阶段
律学在秦汉时期的诞生,以秦代法律注释书《法律答问》等的出现、西汉和东汉相继展开的以经释律、以经注律活动等为主要标志。律学在这一时期滥觞,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首先,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政治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以及国家的制度设计的日益完备等,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其次,这一时期成文立法的发达、立法活动的频繁以及法律数量的日益庞杂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客观的需要。再次,秦汉时期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经学的发达以及语言学、文字学和逻辑学的进步为以法律注释活动为主要表征的秦汉律学研究的展开创造了适宜的文化环境。
作为以法家理论治国的典型,秦王朝虽然由于其高压的集权统治而对几乎所有的学术研究活动均予以取缔和镇压,但却异常重视法制,实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国策,从而为律学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国家支持(以《法律答问》为代表的法律注释书的风行即是很好的例证) 。尽管秦代律学由于缺少其他的学术支撑而在表现形式上仍略显稚嫩,但它却为两汉时期律学的持续的开创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汉朝建立后,经过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两汉的统治者逐渐认同并采用了“外儒内法” 、“霸王道杂之” 、“德主刑辅” 、“明刑弼教”的治国方针,通过说经解律、引 礼入法以及推行春秋决狱等,把封建法制与儒家伦理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开始了封建伦理法制化、封建法制道德化的进程。因应这种时代的政治背景,两汉时期的律学研究也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突出表现为董仲舒等儒家经学大师的以经释律及东汉学者将经学方法应用于律学研究并进行的以经注律的实践。如果说西汉的律学研究因为克服了一味用刑的缺陷而培植了较为厚实的理论基础,那么东汉时期通过训诂方法(经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律学研究则变得更为系统、周密和严谨。据《晋书-刑法志》载: 对当时(汉)的律文“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 东汉学者的律章句,是东汉时期最典型的律学著作,为秦汉时期律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儒者们通过律章句对汉律令中的概念、立法背景和历史渊源等均作出了各自比较精确的界定和阐述。
比照初萌期的律学,秦汉诞生期的律学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首先,它内容更加丰富,注释也更为详尽。秦汉律学有对某项法律、法令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演变的阐述分析,有对律文的立法宗旨、含义的归纳总结,还有对法律概念、术语的训诂、解读和界定,呈现出一种较为系统的状态。其次,律学研究中儒法合流的趋势明显。秦代律学对宗法伦理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如秦律规定:“父盗子,不为盗。”而两汉时期法制的儒家化更使律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儒家的思维与视角所同化。汉时的儒者不仅用儒家经义来阐述法律文意,而且用经学方法来诠释法律概念。再次,秦汉律学开创了立法与编撰律疏同时(如秦朝的《法律答问》)、法律注释与私学并行和前文已述的以经释律等传统,这些都对后世影响极大。
3.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
尽管律学于秦汉时期诞生,但对律学研究予以明确记述并使用“律学”来指称法律注释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却是魏晋以后的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的过渡性演变时期,秦汉早期的封建法制经由它完成了向成熟完备的隋唐封建法制的转变。在长达近四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封建集权统治的相对削弱及周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整个社会的结构(包括文化结构)在剧烈的变动中得到了新的整合。因应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律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独立性明显增强并呈现较前代更为昌盛与活跃的形态。主要表现在:
〈1〉儒家思想在律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律学研究儒家化基本完成。可以说,律学的诞生过程,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也是律学研究儒家化趋势日益发展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在国家立法、司法活动中,在社会的律学研究中的影响,不仅较秦汉更加广泛、深入,而且出现了系统化、制度化的倾向,为隋唐及后世律典的“一准乎礼”奠定了基础。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这一时期“十恶”、“八议”等的出现以及围绕“十恶”、“八议”的入律,律学家们从经义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的深入研究和阐述。
〈2〉律博士的设置和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的形成。
公元227年,卫觊上奏魏明帝:“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魏明帝采纳了卫觊的建言,于是曹魏在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9年)颁布《新律》的同时,在廷尉之下,置律博士一人,位第六品中中,负责对地方行政官吏和狱吏教授国家的法律、法令。此后西晋及南北朝时期的政权也大都设有律博士或类似职位。魏晋南北朝的律(学)博士,是在司法机构廷尉或大理寺之下的属官。这样,法学教育附属于司法行政之下,律博士们既研究、教授法律,也参与立法与执法活动。又据史书载,后秦姚兴当政时期(394-416)于长安设立律学,“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 这是中国历史上官方设立的第一个独立的法律教育机构。律博士和独立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的设置,使律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偶然自发的状态和单纯的学者热情而具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对促进这一时期律学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名家辈出与律学地位的提高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名家层出不穷,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职业阶层。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曹魏时期的刘劭、卫觊,西晋时期的杜预、刘颂、张斐,南北朝时期的封氏家族等。律学家们或直接参与当朝立法,或对成文法典的条文做出权威性的注解——这些注疏经由官方认可甚至可以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法律文件,从而使律学在社会上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律学研究在国家法制建构中的作用也日益彰显。例如律学家杜预曾直接参与《晋律》20篇的制定工作,而由封述(出身渤海律学世家封氏家族)主持完成的《北齐律》则取得了这一时期立法的最高成就。又据《晋书-刑法志》载,太和初年,魏明帝下诏要求各级司法官吏在审判活动中“但用郑氏[注:指郑玄]章句[以经释律著作],不得杂用余家”,这一规定使私人对法律的注释在历史上首次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司法文件。当然,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律疏注释成果当属张斐、杜预两位律学家对《晋律》所作的注本和律解。他们的晋律注经晋武帝诏颁天下,具有了与法典律文条目相同的法律效力,以致后世径称《晋律》为“张、杜律”。
〈4〉方法论的进步和律学研究的深入与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晋代以后,由于玄学宇宙观和“辨名析理”方法论的影响,律学研究在方法论上有了进步。律学家们一般不再单纯使用儒家经义来解释法律条文和法律名词,而是更多地使用抽象的逻辑思维及归纳、演绎的推理方法,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逻辑化、抽象化、系统化的趋势愈加明显。
在方法论进步、法制发展、文化昌明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律学在研究上愈加深入繁荣,其成果集中表现于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立法改革与创新之中。其一是魏晋律的制定和刑名法例篇的定型;其二是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于世的并为隋唐律典十二篇目、五百条文的结构体系提供了直接历史渊源的《北齐律》的制定。
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的独立与勃兴,除了上述四点表征,还表现为刑法原则的确立与完善、法律解释的精确与明晰等等,笔者限于篇幅,此不赘言。虽然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有着浓厚的承启性色彩,然而毋庸置疑,其在整个律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重要而关键的,而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革新法制方面的独特的开创性的贡献在中国古代律学史、法制史中无疑将永放光芒。
4.成熟与发达的隋唐律学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封建法制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空前的完备状态。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因应立法发展、法学教育全面展开、法学世界观进一步成熟的时代法制背景,在总结吸收前代律学成果的基础上,律学在隋唐时期步入了历史性的成熟与发达阶段。主要表现在:
1)官方及私家编纂的律学著作为数众多(代表性著作为唐长孙无忌等人奉诏编著的《永徽律疏》)且社会普及度较高;
2)以儒家为核心并综合各家精华的封建正统法学世界观全面渗入到律学的研究之中 3;;
3)律学研究中有关法律体系的理论进一步成熟,体现立法学成果的法典的结构也更为合理;
4)刑法的基本原则更为丰富,刑罚的体系更加完善;
5)专门性法律制度的研究更为深入;
6)律文注释更为全面(如在阐述“十恶加重”原则时,唐律疏议对“十恶”重罪的立法意图和宗旨均作了详尽的说明和论证,并阐释了与之相关的皇权原则、宗法伦理原则及贵贱尊卑等级原则等),法律名词概念的解释更为精密周全(如唐律疏议在探讨“罪刑法定”问题时虽然指出:“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制敕,量情处分”,但同时也认为人主之断为个案,强调“不得引为后比”);
7)律学研究的方法更加多元。
隋唐律学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巅峰时刻”,而作为中华法系的标志性律典和人类历史上三部最杰出的法典之一的《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则是这一时期律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从唐律的结构体系看,作为中国古代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其序列安排是十分合理的;它以“刑名法例为首,实体犯罪居中,诉讼程序置后” ,整部法典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充分体现了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立法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与创新。 前人有言,唐律“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范围甚详,节目甚简”。的确,唐律不愧为我国古代法学世界观和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继承了历代立法的成果,其本身又有所发展和创新,从而达致了封建立法的最高水平,为唐代封建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在后世中国及东亚、东南亚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当社会稳定发展、成文立法发达,讲求“法条之所谓”的律学便会兴旺。隋唐律学的成熟与发达,尽管有其历史积淀的因素,但也正是上述规律的具体体现。当然,律学在隋唐时期的成熟与发达已经有着浓厚的总结性色彩,而其在唐之后的衰微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物极必衰”的哲理——然而这却并不构成我们置疑隋唐律学之辉煌成就及其历史性地位的理由。
5.走向衰微——宋元时期的律学研究
唐朝灭亡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由动荡的五代十国进入到了地区局势相对稳定的宋辽夏金元时期,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多元法制并存阶段(其中宋元法制较为完整)。这一时期的律学研究较之隋唐,其形衰式微的趋势明显。然而独特的社会时代背景赋予宋元时期律学以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其时斑斓的封建后期法制的建构。
终两宋之世,律学兴废几番,其路坎坷。律学教育在宋朝有三次大规模的兴起,即所谓的“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及“崇宁兴学”,这三次“兴学”可以认为是两宋读书读律风行及律学研究较为活跃的时期。然而,尽管宋朝统治者对当时的读律之风予以了肯定,但其在设置律博士和官方法律教育机构“律学”问题上的游离不定的态度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律学的发展4 。再加上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日益确定、两宋时期对总结司法审判经验的异常重视 以及宋代司法中敕的风行等等使得律学在两宋时期事实上沦为“小道”。然而即便“落寞”如斯,两宋律学依然在历史上绽放出了其独特的光彩,突出表现在有宋朝特色的立法成果《宋刑统》之中。《宋刑统》由宋太祖时期的朝廷司法官员和法律专家受诏编撰,经由太祖皇帝诏颁天下而成为两宋通行全国的刑书类型的根本大法,其独特之处在于:1.采用刑律统类的形式 ,不仅是中唐以来立法编撰形式的一次重要变化,而且也是对传统的封建律典命名的革新。2.添附敕令格式的体例,首开我国立法史上律令敕式合编体例的先河。《宋刑统》不仅在两宋时期得到实施,它还影响到了辽、金、元至明清时期甚至于东南亚诸国的立法,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朝律学研究的独特的富有开创性的成就。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10
结字“五论”
1.紧凑立形论
古今书论中所涉及汉字结构的要点很多,何为最基本的汉字结构规律,何为一般规律,至今仍悬而未决。
仔细观察和分析就会发现,写出的字难看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结构松散所致。由此可见,汉字结构最主要、最基本的矛盾是“聚”与“散”。聚与成形,立以成物,无聚则无形,无形则无立。万字聚为先,聚为万字先,无聚不成字,成字必先聚。就此,笔者提出“米”字聚法。顾名思义,所谓“米”字聚法是指以“米”字为代表,体现“紧凑立形”理念的汉字结构法则。其要诀为:上沉下升,左右相靠,错位穿插,有机聚合。“米”字聚法包括独米、上米、下米、左米、右米及各自核心内容的扩展和延伸。它们分别代表五种不同“聚合”方式的汉字。换言之,所有汉字均可按此五种不同的“聚合”方式对号入座。
具体而言,独米的结构要诀为“八方相聚,内紧外展”,上米、下米的结构要诀为“上沉下升,错位聚合”,左米、右米的结构要诀为“左右相靠,错位聚合”。
“聚”有聚形(形聚)、聚心(心聚)之别,聚形是手段,聚心是目的。
2.比例定量论
通过调整字根(一字中相对稳定而独立的笔画组合)与字根、字根与整体之间平面占有量的分配,达到视觉上协调相称、和谐相处之目的的做法,即为比例定量法。我们已知的比例仅有正比、反比之说,并无主次之分。而在书法中,这种主次是客观存在的。
何为主比例,何为次比例?对于上下结构的合体字而言,上下结构之间的长短之比即为其主比例,而上下结构之间的宽窄之比则为其次要因素,即次比例。主比例、次比例是一个可变动的概念,它随合体字结构类型的不同而不同,随合体字结构类型的变化而变化,二者主次分明,互为补充。
3.相称定位论
“匀称”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匀称”主要包括比例、相称两项内容,而狭义上的“匀称”仅指相称。比例是广义“匀称”的主体和主导,其作用和意义在于决定汉字结构各部分的平面占有量,即“定量”;而狭义的“匀称”(相称)则决定汉字结构各部分之间的上下或左右位置关系,在广义“匀称”中居辅佐、次要地位。广义“匀称”是比例加相称,即定量加定位。无量则无位,有位必有量,二者互为存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4.重心核心论
以往关于汉字结构重心的论述,多强调汉字应有中心或斜中求正,忽略了汉字重心最基本的内容。笔者以为,树立中心或斜中求正乃汉字重心的外在形式,核心方为汉字重心之基本内容和基础。重心随核心的存在而存在,随核心的移位而移位,随核心的消失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核心是重心的代名词,是重心的灵魂。“聚”的结果未必产生中心,但必然造就核心。“重心核心论”即是对汉字结构“聚为万字之本”的又一次认同和肯定,同时也是“聚为万字之本”的延续和引申。
5.变化主次论
艺术,异术也;艺术,变术也。“变”是艺术之宗。书法艺术是通过形态的变化,即笔画、字根、结构、字形的变化达到意趣变化之目的。书法所涉及到的变化要素很多,长期以来,其内容存在交叉、包容的“多栖”现象,故有必要对其加以梳理、整合、归纳和概括。
笔者认为,“主次”是汉字结构变化的主导和主线,其它皆为补充和完善。“主次”的主要表现为:上次下主(上小下大、上让下占)、左次右主(左小右大、左让右占)。对比是变化的主要手段,主次是变化的主要内容。
结构规律
结构规律是一个总体概念,包括基本规律和一般规律。“米”字聚法(紧凑)为结构的基本规律,比例恰当、位置相称、重心平稳、变化生动为结构的一般规律。“聚而变”提示并记录结构规律“聚以立形,聚而求变”运行的全过程,是对结构规律一言以弊之的高度概括,具有提纲挈领、画龙点睛之作用和意义。
在寻觅不到结构规律,特别是基本规律的情况下,“结字难”的客观现实迫使人们把掌握结构规律的希望寄托在某种写字格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效果如何呢?无论是历史、现实,还是哲学和常识都已经而且还将继续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万能的汉字写字格,最好的格是心中之格、意中之格、手中之格、规律
之格。
书艺“三法”
笔法、结构、章法已被广泛认可为书法的三项基本内容,但其框架至今仍处于主角空缺、正谬混杂的无序状态中,实为一大憾事。古代虽有“永”字八法,但无论是从字面含义还是从其效果看,都是重在阐述汉字八种基本笔画以及由此八种基本笔画衍生出的几十种笔画的外在形态。可见,“永”字八法为外在形态之法,而非本质内藏之法。再者,结构、章法为何法?答案空缺,至少是概念、称谓上的空缺,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有鉴于此,笔者以“一”字藏法、“米”字聚法、“森”字变法为例予以说明。
书法意义上的笔法之本非“藏”莫属。在此,笔者取汉字中最简单、最具代表性的“一”字为其代言形象,称之为“一”字藏法。“一”字藏法与“永”字八法并不矛盾,前者为本质内蕴之法,后者为外在形态之法,二者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如前所述,“米”字聚法其本在“立形”,这里不再叙述。
章法就是书法大形象而言的,其实质是“变”,“变”是章法之本。笔者选取汉字中最能代表变化的“森”为其代言形象。理由是,它由三个常用字“木”组成,分别处于上、左下、右下三个不同方位,其大小、形态各异,彼此之间存在可比性和最大程度变化的可能性。
概而言之,“一”字藏法,指以“一”字为代表,体现逆入平出、藏头护尾特征的运笔法则;“米”字聚法,指以“米”为代表,体现上沉下升、左右相靠聚心特征的结构法则;“森”字变法,指以“森”字为代表,体现违而有序、变化生动特征的章法
法则。
结构是书法技法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在汉字结构的教学上,教师无“法”可依,学生无“规”可循,由此造成教学效果不佳。从这个意义上讲,探索可行的结构规律是现实的客观要求。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书法院))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学生汉字规范书写与书法教育研究”(12YJCH157)阶段性成果之一;2012年度甘肃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甘肃省大中小学生汉字规范书写与写字课教学研究”(2012GSGX048)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11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125-05
“明法”选任是秦汉仕进制度的组成部分。这一选举途径深刻影响着秦汉王朝官吏的知识结构和人员的构成比例,对于我们探讨这一时期人才选用的标准以及人才的培养与任用,非常重要且必要。学术界对此并未予以充分关注,笔者不揣浅陋,陈述管见,敬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
20世纪80、90年代,学术界在深入探讨秦汉时期选举科目时,针对“明法”选任的性质大致提出了三种观点。
其一,认为“明法”为察举科目,并且是察举特科。①
其二,黄留珠先生曾总结了秦代三种“通法入仕”的途径,即法官法吏制、国君举任制以及“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中,法官法吏制又分为两类情况:一是由通晓法令者直接被任命为法官法吏;二是限期习法达到标准者得以递补。②
其三,方北辰先生提出西汉丞相府、东汉三公府以“四科”征辟属吏,③阎步克先生也认为“明法科”的性质为征辟制④。阎先生进一步指出“四科”是汉代总体选官的标准或原则,而其中的“明法科”包括三种选任途径:一是察举科目中的“明法”和“治狱平”;二是廷尉正监平、御史、洛阳市长丞、符玺郎,以“明法”为选任标准;三是地方郡县机构辟召决曹、狱吏,也以“明法”为标准。廖伯源先生指出,官府属吏可经由“四科”察举转任朝廷命官,⑤可补阎氏之说。陈蔚松先生主张“明法”是汉代察举特科,但是又提出汉代选官“杂途”中有“吏道”,即居延汉简官吏名籍中考核官府属吏“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⑥对阎氏“明法”标准之说有所发展。
在上述研究中,观点一与观点三的立论基础分别建立在对汉代的察举与征辟两项选官制度的剖析之上,它们对“明法”科的阐释各有所据,所得出的结论却是对立的。观点二的研究未言及“吏道”,实则“吏道以法令为师”在秦汉时期长期适用,对此简牍资料已经提供了颇为充分的力证。以上三种说法,都有失偏颇,不能言明秦汉时期“明法”选任的实质。同样,虽然阎氏与陈氏所论秦汉时期官吏选任以“明法”为标准或条件之说颇有见地,但是将“明法科”等同于“明法”选任,则忽略了非“明法”科中选任“明法”人才的仕进途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明法”选任进行深入地探讨,阐明秦汉时期以通晓法律为标准选用人才的途径及其相关制度。
二
秦汉“明法”选任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可以上溯到秦孝公颁布的“求贤令”。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孝公“求贤令”下,他以游士身份入秦,经由景监举荐,游说孝公变法,出任左庶长,主持秦国的变法。这在春秋战国时期是较为常见的选贤任能途径。“求贤令”的特殊性在于,商鞅为法家,他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制定法律。可以说,商鞅变法开启了行政运作以法律为依据的序幕。秦统一至两汉,“任法为治”的统治模式被继承和发展,以“明法”为标准构建出一系列选任制度。这一时期,“明法”选任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以“明法”为科目的选任制度;二是以“明法”为标准的选任制度。我们先对后者加以分析。
其一,帝王召选与私人举荐。据《史记・蒙恬列传》,秦王闻赵高“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学者称其为“通法入仕”。⑦汉宣帝即位,闻河南太守丞黄霸“持法平,召以为廷尉正”⑧,秩级从秩六百石超迁为秩千石。东汉初,廷尉曹史张禹善于处理疑狱,光武帝“册免廷尉,以禹代之”⑨。由最高统治者直接选用法律人才,体现出“明法”选任备受关注的程度。与此同时,秦汉时期由私人举荐“明法”者也屡见不鲜,著名者如:景监举荐商鞅,丞相翟方进举荐“明习文法”的薛宣,⑩司徒刘恺举荐“明习法律”的廷尉正。被举荐者包括未仕者、免官者、官府属吏;举主或为君主近臣,或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举荐为被举者仕宦增添了砝码。与此同时,保任法也保证了正常情况下被举者多名副其实。
其二,“举贤良”为“明法”者仕宦提供了新的途径。汉文帝十五年(前165)诏举贤良,学习申商刑名的晁错被举为贤良,以对策高第由太子府家令迁为中大夫。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丞相卫绾奏请罢免治申、商、韩非之言者。此后的贤良选举中,仅有公孙弘、王尊曾传习律令,而且二人应举与其“明法”无直接关联。显然,“明法”不再被列为“举贤良”的标准,“明法者”应举的情况随之骤减。尽管如此,“举贤良”在“明法”科目形成时被有选择地保留并不断完善。
其三,“明法”选任中的世官制遗绪。尽管商鞅变法打破了秦国世官制度,但是其遗存作为补充形式长期存在于政治生活中,尤对“明法”选任影响深刻。据《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蒙恬“尝书狱典文学”,具备“明法”的素质,他“因家世得为秦将”。汉代子弟通过家学、吏学通晓法律,进入仕途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有子承父业者,如张汤父为长安丞,学书狱,“父死后,汤为长安吏”;于定国父于公为郡决曹,“少学法于父”,“父死,后定国亦为狱吏”;王霸“世好文法”,“祖父为诏狱丞”,父为郡决曹掾,“霸亦少为狱吏”。有学于官府者,如严延年父为丞相掾,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有世传律令,世为官宦者,如杜周为酷吏,二子“治皆酷暴”,少子杜延年“亦明法律”,昭帝初以杜周子得补军司空;郭氏“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着甚众”;吴雄,“子孙恭,三世廷尉,为法名家”;陈宠曾祖父陈咸“以律令为尚书”,他“明习家业”,子忠“明习法律”。秦汉时期,二千石以上的官吏有任子之制,而一般的“明法”吏员,则通过家传法律或至官府传习法律将其子弟引入仕途。睡虎地秦简《内史杂》规定:“令史毋从事官府。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这样,“史子”学于官府,得到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二年律令・史律》对“史子”为学童及任用立法加以规范。显然,“明法”官吏的子弟符合秦与汉初“史子”学于官府的法律规定,同时也使“明法”吏员子弟可以子承父业,造就了许多“明法世家”。
其四,吏师制度下的“明法”选任途径。秦汉时期,不仅官吏子弟可以在官府接受法律教育,而且在吏师制度的影响下,更多的吏民通过“宦学事师”得以“明法”,进而出师、仕宦,这在整个“明法”选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文帝时廷尉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蜀郡守文翁派遣郡中小吏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路温舒“求为狱小吏,因学律令”;尹翁归“为狱小吏,晓习文法”等。吏师制一方面为法律人才提供了仕宦的平台,另一方面又承担了一定的“明法”教育的责任,对于“文法吏”整体素质的培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五,考课制度下的“明法”选任途径。汉代仕进制度“选举与考课不分”的特点使“明法”者凭借课最和累积功劳得以选任。如:刀笔吏出身的萧何“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西汉文帝时,“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东汉北海敬王刘兴“为人有明略,善听讼,甚得名称”,“迁弘农太守”。其他还有赵禹“以刀笔吏积劳,迁为御史”,丙吉“治律令,为鲁狱史。积功劳,稍迁至廷尉右监”。此外,在居延汉简中,中劳与“颇知律令”是燧长、候长、有秩士吏等上计考课的基本内容。对于在中央与地方任职的“明法”者而言,不论是课最还是累计功劳,都是其升迁的基本条件,由此形成了“明法”考课的仕进途径。
“明法”选任的标准在非“明法”科目中广泛应用,有效地拓展了法律人才入仕和官吏法律素质的养成。诸“明法”科目的制度规范具体如下。
第一,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规定丞相府以“四科”选任属吏,第三科为“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入选者“补四辞八奏”。东汉“世祖诏”中重申“丞相故事,四科取士”,同时新增“孝悌廉公之行”作为基本要求。章帝建初八年,再次颁布诏书,以四科辟士,尤其针对“郡国举吏”。征辟取士的人选需要借助荐举、察举、征召、吏师、世官、考课等途径提供。在人才选任的程序上,突出“明法”者“文中御史”的才能,量才授官。
第二,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诏令州郡察举茂材。据卫宏《汉旧仪》记载,“刺史举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设“明律令一科”,“选廷尉正、监、平案章,取明律令”。此科的选任程序包括察举、科考和任用三个环节。刺史负责察举环节的推荐和保任,丞相负责考选环节与选任环节,实现依科选用人才。“明法令”与“明经”、“治剧”并列为三科,这与丞相府“四科取士”相比,在科目性质、举主身份、选任程序和任用上都有很大不同,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了“明法”人才的专业素质,这也正是任职所必须的知识与能力。
第三,平帝元始二年,“中二千石举治狱平,岁一人”。李奇注曰:“吏治狱平端也。”“中二千石”负责察举,说明“举主”以九卿为主;“岁一人”,表明其为岁举科目。此项“明法”科目的执行情况史书记载不详,但是从举主秩级看来,是规格较高的察举科目。
第四,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文吏”,是指能够胜任治狱职责的官吏,法律素养必不可少。试笺奏,在很大程度上是考察应举者依据法律规范处理各项行政事务的能力。阳嘉新制中“文吏能笺奏”的改革,在考试内容、察举程序与选任方式上都有所调整,力求察举名副其实。
三
秦汉时期,“明法”选任为法律人才铺就了出仕、迁任的路径。阎步克先生认为秦王朝行政依赖于“法吏”、“狱吏”,而汉代行政则由儒生、文吏共同承担,这种观点颇具启发意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进一步探讨“明法”标准的调整情况,从而深入分析秦汉时期法律人才的政治定位与社会期许的变化,以及由此对“明法”选任制度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商鞅变法以降,秦国统治者推行“任法而治”,当是时,“明法”包含了通晓法家学说与商君之法二端,由此“明法”者的范围从倡导法家学说的政治家扩大到处理日常管理事务的各级官吏。基于国家行政的需要,荐举制、世官制、吏师制、考课制、征召制,都将“明法”作为一项选官标准。
“明法”选任在秦统一前后经历了一个较为特殊的发展阶段。秦国在兼并战争获得阶段性胜利后,就将其统治模式推行到其统治区域内。睡虎地出土的《语书》中,郡守腾在秦并南郡不久就地方政令,强调“凡法律令者,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墓主喜在秦王政时期,先后出任过安陆令史、鄢令史,县级属吏随葬的律文却计有《秦律十八种》125条、《效律》22条、《秦律杂抄》27条、《法律答问》、《封诊式》等。可见,秦国地方机构由行政长官在郡县推行“以法为教”,县属令史也掌握大量涉及行政管理的法律知识。统一六国后,其行政也延续了“事皆决于法”的法家统治模式,尚严酷,“以任刀笔之吏”。通晓法律的“刀笔吏”与“学室”弟子中的“明法”者分别成为国家选用与培养的人才,使法家“一断于法”的政治理念被推向极致。
西汉初年,虽然黄老之学倡导“无为而治”,但“萧规曹随”的统治形式基本沿用了秦代法家的模式。尤其是“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景帝“不任儒者”,都为“明法”者仕宦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如文帝诏书中提出“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景帝在诏令中言“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在法律人才选用上,文帝时吴公以“治平”出任廷尉,同样出任廷尉的张释之,坚持法信于民,以持议平为天下所称道。引导“明法”标准从“文无害”转向“治平”,实际上对法家崇尚严刑峻法的价值观进行了修补,这不能不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汉武帝以降,统治思想从黄老无为转变为“霸王道杂之”,霸道用律,王道用经。随着“明法科”的设置,加之宣帝于地节三年(前67)设置廷尉平,地节四年诏令丞相御史以“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以及皇帝征召、世官制度、吏师制度、考课制度中的“明法”选任途径,共同构成了“明法”选任体制。选任标准也以“通晓法令”、“明习文法”取代了申、商、韩非之学。成帝时薛宣提出的“吏道以法令为师”与秦墓出土《为吏之道》中以是否“明法律令”作为衡量官吏“良”、“恶”的标准,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从选任“四辞八奏”到“廷尉正、监、平”,再到“治狱平”、“文吏课笺奏”,“明法”由官吏的基本素养下降为断狱决疑、处理行政公文的职务技能,从而导致了法律人才的政治定位和社会期许由富国强兵的革新者,一变而成为统治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再变而降为处理法律事务和行政程式的吏员,削弱了“明法”标准在官吏仕宦中的影响。但是“明法”选任提供的法律人才通常在行政中发挥的作用,往往是诸生或其他学问的传习者以及以品行见称者所不能企及的,反映出“明法”者在秦汉行政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秦汉时期“明法”选任形成如下认识。
其一,“明法”选任囊括了秦汉时期法律人才的培养、考核、任命一系列建制。在人才培养方面,“明法”官吏家庭与学室、吏职分别承担了部分法律教育的责任,世官制度下的“明法”选任、吏师制度下的“明法”选任以及官吏试守制度,将法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且“明法”选任途径与科目对法律传习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这些共同促成了秦汉时期法律在官学与私学教育上的兴盛。在人才考核方面,学室的考试制度,“明法”课最与功劳累积,以及“明法”科目中的考选,对法律人才的知识与能力进行了综合的考察,将考核制度与选任制度合而为一,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选用能够名副其实。在人才任命方面,“明法”选任由属吏辟除、考课迁任、察举征辟科目的选任共同组成。“明法”选任制度构成的丰富,是秦汉时期官制发达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秦汉时期统治者非常重视法律人才的选用,通过各种制度保证法律人才顺利入仕、升迁。
其二,“明法”选任制度是秦汉日常行政管理的新陈代谢机制。商鞅变法以来,秦国的各项行政事务被纳入到法律的规范之下,通过“明法”标准选用法律人才,可以有效地维护统治机构的正常运作。在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教政策,更是将“明法”作为官吏选任的唯一标准。西汉初年,基本承袭了秦代的统治模式,“事断于法”成为官吏通法仕宦的前提。汉武帝以后,推行“霸王道杂之”的路线,法律的权威性受到经义的冲击,“明法”选任也在一定程度上遭遇“明经”选任的影响。尽管如此,“明法”选任并未被废止,反而与“明经”选任并行,这进一步说明“明法”者解决行政事务的能力不容小觑,“明法”选任依然发挥选贤任能的作用。秦汉时期,正是通过“明法”选任,促成了法律人才的有效流动,由此对行政机构的运行与统治秩序的稳定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三,秦汉“明法”选任制度发展的趋势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秦汉时期,“明法”选任的兴起,是商鞅变法的产物。汉武帝以后,“明法”选任在发展进程中就遇到了诸多问题,分别是“明法”价值观的二元化,文法吏价值取向的功利化,法律知识的技能化,以及选官标准多样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背后所隐藏的深层次根源,是秦汉时期统治模式的震荡与调整。为了契合政治需要,“明法”选任的标准适时进行改进,选任的范围日益受到限制,选任的颓势已经逐步显现。除了“明法”选任在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统治形势的巨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进程。西汉后期法律人才不仕莽朝尚可归结为暂时现象,但是到东汉后期,王朝统治江河日下,统治秩序濒临崩溃,法律以及其他各项维护统治的工具都失去应有的效用,进一步加剧了“明法”选任制度的衰落。
汉代的法律形式篇12
随文识字是把生字放在特定语言环境中感知、理解、掌握,使每节课的教学内容多样化,学生动脑、动耳、动眼、动口、动手,全方位参与,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利于听、说、读、写等语文能力的培养,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意识,符合儿童学习语文的规律。相对于孤立识字,其明显的优点是:生字新词的出现和理解都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进行,有利于借助语境来记忆;将识字与读文紧密结合,有利于实现汉字识别自动化,大大缩短了从识字到阅读的转换过程,有利于学生尽早阅读,借助规范优美的书面语材料,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总之,运用随文识字方法,能够将汉字的音形义结合起来,能够将学与用结合起来,有利于学生语言的发展。
二、随文识字的“漏洞”
施茂枝先生说:“一个成功的识字教学体系必须遵循汉字的规律、汉字识记的规律与书面语言学习互相促进的规律, 并努力使三者形成合力。”[2]从这个层面看,随文识字在汉字的规律、汉字识记的规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漏洞”。
1.生字编排违背规律性
随文识字以课文为载体编排生字。从现行教材来看,生字的编排基本上是“打乱仗”,没有(或者说较少)考虑汉字本身的系统性。如人教版《语文》(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后文简称“教材”)一年级上册第1课的课文是《画》,要求认识的生字有“远、色、近、听、无、声、春、还、人、来、惊”,会写的是“人、火、文、六”,其中“火、文、六”是在拼音教学、集中识字等内容中学过的,前面认,后面写,这个符合认知规律。但是本课的生字中,除了“远、近、还”有共同的意符“辶”,“远”、“近”意思相反(反义词)外,其他的几个生字之间并无任何联系,无论字音、字形、字义都各自独立,不成系统,没有什么规律可循。这样,学生就得逐个学习、逐个记忆。这无形增加了学习负担,影响了识字效率。
还有,教材中生字的编排很多都不符合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规律,而是先“难”后“易”的。比如教材还没安排学生学习“元、斤(一年级下册语文园地二里学习‘元’,二年级上册识字5里学习‘斤’)”,就先学“远、近”了;一年级下册第20课里有生字“慌”,到二年级下册的“语文园地二”里才安排生字“荒”。这既不符合汉字本身的规律,也不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自然增加了汉字学习的难度,影响了识字效率。
2.教学方法忽视规律性
随文识字主要借助汉语拼音学习字音,结合课文内容理解字义。可是绝大多数汉字不止一个义项,而且小学课文中的字义往往不是本义,而是引申义,这自然影响到了字形与字义的内在联系。再加上很多教师不能根据字理将字音、字形和字义联系起来教学,更增加了识字的难度。比如“初”是会意字,从刀从衣,表示用刀剪裁布料是做衣服的第一步,本义是制衣之始,引申泛指一般的起始、开端,如“起初”“初学”,又引申出第一个、第一次、原来的等义。很多教师不懂“初”的形义关系,只好反复给学生强调该字是“衤”旁,不要少写了一点成了“礻”旁。苦口婆心,费力费时,结果却是很多学生照旧写错这个字。
听课时,常常见到类似的记忆字形的方法:“十颗豆子落口里(喜)”“每天都要戴草帽(莓)”“土里不长东西(坏)”“火山爆发,大火把山烧倒了(灵)”……这种“一字一故事,一字一说法”的识字方法,对帮助学生记忆个别字的字形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完全脱离了字义,明显违背了汉字的规律性,支离破碎,不利于学生将字形与字音、字义联系起来理解、记忆,严重影响了汉字的运用,自然为错别字的产生埋下了“祸根”。
三、随文识字的“补丁”
发现了“漏洞”,就需要增加“补丁”以便及时修补,否则有可能因小失大甚至导致“崩溃”。究竟如何修补呢?当然需要“对症下药”,既然“漏洞”出在规律上,那就在规律上做文章,加强规律性。
1.从教材入手
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内容的载体,是借以实现语文教学目标、发挥语文教育功能的物质基础,具有凭借、示范、教育等作用。因此,教材内容一定要科学,要符合学科规律和认知规律。
(1)生字的编排要循序渐进。学习从来无捷径,循序渐进攀高峰。《礼记・学记》要求“不陵节而施”。朱熹提出“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这些都告诉我们:教育要根据学习者的年龄、基础、智力等因素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不超越学习者的接受限度。教学如果不能按照一定顺序而是杂乱无章地进行,学生就会陷入紊乱而没有收获。
如前文所言,目前小学语文教材中生字的编排类似于一年级学“慌”二年级学“荒”的先难后易的现象随处可见,这就违背了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必须纠正。笔者认为,无论从汉字本身的规律性还是识记汉字的规律来讲,生字的编排都应该由易到难,先学独体字,再学合体字。首先以集中识字的形式,编排常见的尤其是那些具有很强构字能力的独体字,其次以字族文识字的形式,根据汉字的构字规律,运用以熟带新的方法编排合体字,同时以随文识字的形式,结合课文编排生字。这样既省时又省事,既科学又可以培养学生的能力。
(2)增加集中识字内容。美国心理学家米勒提出组块的概念。他认为,对信息进行组织,使其成为组块,会扩大该系统的容量。然而,随文识字中生字的编排很难兼顾到汉字的系统性,无法“组块”。单篇课文中的数个生字之间并无音形义诸方面的内在联系,即使扩大到一个单元、一册书中的生字,依然不能构成系统,学生只能一个一个孤立地识记,自然影响效益。
裘锡圭先生告诉我们:“跟文字所代表的词在意义上有联系的字符是意符,在语音上有联系的是音符。”“汉字的字符里有大量意符。传统文字学所说的象形、指事、会意这几种字所使用的字符,跟这几种字所代表的词都只有意义上的联系,所以都是意符。”“形声字的形旁跟形声字所代表的词也只有意义上的联系,所以也是意符。”“形声字的声旁也是音符。”[3]
如果将裘先生的汉字学理论与米勒先生的组块理念结合起来,按照意符、音符组块编写出科学的集中识字的文本,则可以弥补随文识字的不足。
现行小学语文教材中一般都编排了集中识字的内容,只是太少了,大多安排在前三个学期,而且多半是一个单元安排一次,比如人教版《语文》一年级上册识字(二)、鄂教版《语文》一年级下册识字(三)等,如蜻蜓点水。其实,到了中高年段,同样可以安排集中识字,只是难度要加大一些,要求要更高一些。可以利用汉字的构字规律编写韵文,以便“组块”识字。比如:
短尾鸟儿名叫隹,
它的朋友一大堆,
隼雀雁雕雄雌集,
崔淮推谁惟维锥。
“x”为水广“ ”通畅,
它们都能做声旁。
梳疏蔬,流硫琉,
竖折无点荒慌谎。
在对小学生的错别字调查中,笔者发现“隹”“x”“ ”都是特别容易写错的部件,“隹”容易少写一横,“x”“ ”的错误出在“N”和“厶”上。其实,“隹”“x”“ ”是三个独立的字,只是在现代汉语中一般不独立使用,但是作为合体字的部件,它们是比较活跃的。上述韵文,充分利用汉字的形声造字规律和构字部件的灵活性来“组块”识字,不仅便于记忆字形,而且便于理解字义,当然有利于减少错别字,提高识字效率。据统计,常用汉字中,大约80%是形声字,这就为类似的集中识字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2.从教法入手
有一句行话叫“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这说明教材编排的不足之处,可以通过科学的教学方法来弥补。随文识字中生字的编排很难兼顾到汉字的理据性和系统性,那么,在教学方法上就要加强理据性和系统性。
(1)加强理据性。现代汉字由笔画或偏旁构成,一个汉字由几笔几画,由什么偏旁构成,有其内在的道理或根据,这就是汉字内部结构的理据性。仔细研究小学生的错别字,就会发现很多是因为不了解汉字的理据而导致的。如写“德”字,往往容易漏掉中间的一横。如果让学生了解它的理据:“德”是会意字,从彳从直从心,强调心正直为德,本义是道德,品行。在此基础上强调右上边的“ ”是“直”的变形,这样就能够减少错误了。再如“崇”与“祟”很容易混淆,常见的是将“祟”字下面的“示”写成“宗”。如果懂得这两个字的理据,就能够避免类似错误了:“崇”是形声兼会意字,从山从宗,宗兼表声。本义是山大而高,如“崇山峻岭”。引申为尊敬,重视,如“尊崇”“崇拜”。“祟”是会意字,从出从示(与鬼神有关),会意鬼魅出来作怪。本义是鬼神制造的灾祸。引申指行动诡秘,不正当,如“鬼鬼祟祟”“作祟”。
在识字教学中,依据汉字因义赋形、形声相益的特性,把握其内部结构的内在理据,建立音形义的必然联系,既增强科学性,又增强趣味性,既有利于理解,又有利于记忆,更有利于运用(减少错别字),可谓一举多得。
(2)加强系统性。系统论原理告诉我们,系统的功能大于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之和。遵循汉字的系统性,势必极大提高识字的效益。汉字总数虽多, 但构字部件却有限。据统计,在常用字中,意符不上200个,音符也只有400多个,相当多的意符和音符具有很强的构字能力,这就形成了汉字内部结构的系统性。系统地学习一串汉字,比孤立地学习相同数量的汉字,效果要好得多。
可是随文识字不可能兼顾汉字的系统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要适时适当进行拓展,让学生以“组块”的形式建立汉字的系统概念。比如“廴”“辶”是容易混淆的两个意符,如果给它们各自建立一个系统,进行对比识记,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廴”本是象形字,是彳的末笔向右拉长的形状,本义是长行,引申为延伸、拉长。在现行汉字中,它只做偏旁,习惯上称为“建字底”。在合体字中做意符,所从字与延长有关,常见字仅有“建、延、廷”三字,另有以这三字做声旁的“健、键、毽、腱、筵、涎、挺、庭、艇、霆、蜓”等字。 “辶”由“u”的楷书草化而成,习惯上称为“走之底”。本是会意字,甲骨文从止从行,本义是走路。在合体字中只做意符,所从字与行走、道路等义有关,常见字很多,如“过、达、迈、迁、迅、巡、进、违、还、连、近、迎、迟、追”等等。这是以意符为中心构成系统。还可以音符为中心构成系统。如以“正”做音符的字有“证、整、症、政、怔、征、钲”等等。
到了小学中高年段,随着识字数量的增加,识字能力的增强,可以引导学生将课内、课外结合起来,以适当的难度作“诱饵”,让他们“跳起来摘苹果”,指导他们根据汉字的规律,以“归类”的方法自主识字。例如,有“氵”的汉字大概有四百多个,大体上可以归为这样几类:
水的自然载体――江 河 海 洋 湖 泊 沟 池
水的静态形式――清 洁 澄 浊 浑 污
水的动态形式――涨 流 淌 溢 漏 滤 泻
水的外化形式――潮 汐 汛 波 浪 漩 涡 瀑 汽
近水的地方――汀 洲 津 滨 渚 涯 滩
水名或地名――漳 浙 漓 沪 潼 渭 泾 渤 淮
水对它物的影响――润 沾 湿 潮 浸 漉
水的容积状态――深 浅 满 沉 沦 浮
像水的液体――油 汁 汗 酒 漆 泪 涕
表示水的声音――汩 淅 沥 潺 淙
人与水有关的活动――汲 浚 沐 浴 洗 渔 漱
这是一种极具知识性、创造性和趣味性的方法,带有研究的特点,用得好,可以大大提高识字速度,提高学生自主识字的能力。
总之,随文识字有它不可替代的优势,但也有明显的劣势。如果能够从教材和教法方面稍加改进,定能提高识字教学效率,进而提高语文教学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