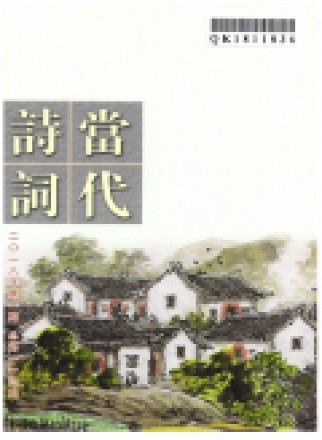当代文学概念合集12篇

当代文学概念篇1
关键词:藏族;当代文学;藏族女性作家
1958年“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正式提出。少数民族文学是80年代后由各少数民族作家以双语或母语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随着少数民族文学的日益规范化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也随之提出,那么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则是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逐渐形成并走向繁荣。继而藏族女性文学的发展也紧跟着时代步伐。80年代后,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中原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藏族女性的生活环境与传统意识发生巨大变化而促就了一批才思敏捷的藏族女作家,她们用女性特有的直觉和细腻写下与男性全然不同的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为主的作品。不论是藏族女性作家的数量和双语的创作现象,还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作品在社会上引起的影响都在当代藏族文学中形成了一个大的气候,但是藏族当代女性文学在藏族文坛中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内容,文化界对“藏族当代女性文学”这一概念有着很多不同的说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其不同说法的根源主要归为:1.对创作主体的性别和民族身份的不同看法2.“双语”的文学创作现象3.对作品内容和题材的不同看法至今对这一概念没有统一的定义。文学作为作家个体体验的凝聚,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文化都无不影响着她,特别是不同性别的作家看问题的立场和角度都不同,从而直接影响着她们的审美意识和作品内容。因此对藏族当代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普遍看法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或生活在五省藏区的藏族女性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文字记载下来的有所有作品都该称之为“藏族当代女性文学”。而这一概念的提出有以下几个意义:
一、 历史意义
20世纪时被称为“西藏奇僧”的根顿群培在《西藏欲经》中指出“私事或是公事,上至贵族或是下至百姓,都不能没有女性”,对女性提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说法,但女性作为人类繁衍的源泉和生活的基石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反而男性一统天下的社会贬低和约束着她们。比如吐蕃赞普时期律法规定“不可听妇人言”,文学作品《五部遗教之王妃篇》中的“女性如毒草,谁食谁便亡”,藏族本有八贤臣可其中唯一一个女贤臣的名字被涂抹而改成“七贤臣”,这一“篡改”历史记载的举动透露着女性不被男性社会所认可和接纳。其次我们再去翻阅藏族文化和文学书籍时发现藏族的整个文化学科都“掌控”在男人的手里,根本没有给女性施展个人才华的空间和任何一个历史责任。因此在藏族古时文坛上根本没有出现过女性的倩影。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藏族知识女性当中极少数人就开始迈入了文学创造的道路,但就女作家人数,或是作品数量来说都没有在藏区引起大的反响,直到80年代后文革的结束和民族政策的优良条件,再加上当时在内地文学界称为“显学”的女性文学的发展大大推动了藏族当代女性文学。藏族文坛中涌起了大批的女性作家,其中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有梅卓、格央、白玛娜珍,用藏语进行创作的作家有白拉、德吉卓玛、华毛、次仁杨尖等。她们用笔杆写下自己的想法和思想把永远处于“沉默”的藏族女性从被描述和被表达的角色转换成描述者和表达者的身份。汉语作家队伍用她们的作品在文字上和其他民族之间架起了“桥梁”,想给了解藏族文学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窗口,母语作家运用母语和女性的视角立场给藏族读者提供了与男作家的作品截然不同的文学作品。因此藏族女性作家作品是藏族当代文学中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不容忽视的。
二、在时代需求下提出的意义
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回顾藏族一千多年的历史时,发现僧俗的男性是藏族文化和文学的主流,女性处于边缘的状态或者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而如今跟随时代的变化和人们思维的搬迁女性不仅参与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与男性争取同等的权利。为此在社会各界各行相继出现了身怀才艺的各类女性。80年代后的藏族女性在文坛中的出现把藏族文学从“单一化”转向多元化,更是符合了“中国当代文学在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大背景下,建立全新的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学”这一口号,并且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下,我们更要坚持内容丰富的藏族文学。比如从70年代开始在“伤痕文学”的主导与作者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下兴起了很多的文学思潮和派别,特别是追求同等权利和性别的差异,表现女性生命意识,女性立场、女性的真实感受的“女性文学”等相继出现在内地文坛,倍受大家的青睐与好评,而在多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藏族当代文学要想发展和更上一层楼的话,必须要坚持藏族当代文坛内部多元一体和共同发展的策略,这是藏族当代文学迈向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和世界当代文学的主要关头,也是藏族当代文学比以前更加丰富和系统化的时代要求。
三、从作品的内容上
不管文学的内容和体裁如何,它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再者它是作者在对客观事物中的感触进过大脑的思考后用文字记载下来的的一种精神上的东西。藏族作家群体中,不管是男女老少,还是僧俗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原因,作品内容上有很多的相似处,这是无法否认的,但由于教育的模式和性别的区别,文学创造的目的和服务对象的不同,他们对作品内容的选材上也有所不同。比如藏族作家群体来讲,在藏族文学中一直处于优势的僧人作家一直生活在寺院,从小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受过教育的男性作家相比较,他们的知识构架、思维方式、世界观都不同,他们的作品内容也不同。前者的内容多半倾向于缘起和性空观等佛教思想,而后者写作的目的是解放人性和描述生活中喜怒哀乐为主。而与两者都有很大区别的女作家来,由于性别生理和社会地位的区别,女性作品的内容大多数是注重女性的命运和生活,她们的内心世界,总是离不开女性。所以女性作家和她们的作品内容在藏族文学史上是一个新颖的内容,有别于男性作家的作品。
总的来说,当代藏族女性作家这样的概提出不管是从藏族文学史上根本没有女作家的历史事实,或在近几年来中国文坛和政策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推动,或是藏族作家从女性的立场和女性独有的生活体验描写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当代文学概念篇2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的形成,实际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若干认识阶段。起先人们用的概念是“新文学”,该概念较早由周作人在《新文学的源流》、[1]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2]等书中使用,此后该概念又为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先生延用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将“中国新文学史”设定为各大学中国语文系主要课程之一,1950年开始撰写,1953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3]王瑶先生用的便是“中国新文学”概念。最早用“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可能是钱基博,他在1930年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丁易在195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概念一直混用,例如直到1979年刘绶松原著,由易竹贤等修订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出版,作者依然延用“中国新文学”的概念,1975年司马长风在香港出版《中国新文学史》[4]也用的是“中国新文学”的概念,及至1980年周锦在台湾出版《中国新文学简史》时“新文学”概念尚在使用中,直到1984年唐弢、严家炎本《中国现代文学史》[5]出版,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概念才差不多基本定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称。
这个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也在变动着。1930年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所述范围,实际以清末戊戌维新起始,“五四”新文学革命为终,1944年任访秋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南阳前锋报社印行)时将“五四”之前的中国文学包含在了“现代文学”中,定为第一编,冠以《文学革命运动的前夜》之名,1980年周锦在台湾出版《中国新文学简史》,又把“新(现代)文学”的概念延伸至1970年代中期。可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现代文学”有不同的界定。这也完全是合理的,1930年代的钱基博眼中的“现代”和1944年任访秋眼中的“现代”、1980年周锦眼中的“现代”自然会不一样。大陆主流学界,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框架的影响下,1949后才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限定于“五四”至“新中国”成立之间的;但是从世界的和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学界在“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限定于‘五四’新文学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之间”的问题上实际一直没有形成统一定识。
从上述过程来看,随着时代和认识的发展,我们尝试把“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作相对调整完全是有历史渊源可循的,也是必要的。目前大陆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成型于1950-1920世纪60年代(1950年,中央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对“中国新文学史课程”内容做了如下规定:“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作家和作品的评述。”这个大纲要求把新文学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论证“新文学的发展是无产阶级占领文学历史舞台的过程和结果”),就如钱基博在1930年写作“现代文学史”的时候不可能把“现代文学史”的范围划定到1949年一样,成型于1950与1920世纪60年代之间的大陆主流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界定,也不可能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范围延伸到1970年代。
进入21世纪之后,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概念,我们会发现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限定于1920-1940年代之间的30年是不合理的――它在两点上显然和我们这个时代对“现代”一词的惯常指认不符:一、它和我们现时代的距离拉开了50余年,1950年代我们称刚刚过去的30年是“现代”还是合理的,就如同1930年代钱基博称刚刚过去的数十年为“现代”也是合理的一样,而现在于21世纪10年代,我们称50余年前的某个时期为“现代”就显得不那么合理了;二、它专指与现时代已有50余年之隔的特定的30年时间,显然也是不合理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历程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一直延伸到当下的过程,它不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就结束了,至少它的范围是30年所不能限定的。就此,重新审视这个概念完全有必要。
二、
20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学实际上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是“五四文学”,一个是“新时期文学”。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五四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特别是从文学精神上来说);“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核心(无论是从文学创作的内在精神还是从文学创作的外在质、量上说都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认为:对“现代文学”学科范围的界定要以“五四文学”的发生、发展、落潮为基本线索;“当代文学”学科范围的界定要以“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发展为线索。
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角度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范围亟待拓展,完全可以拓展到1977年(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新时期文学开始)。目前的“现代文学”概念,只包含1917(以是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标志的中国新文学革命开始)到1949年之间大约30年的时间,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历史纵深以及作家、作品幅员不够,大多数现代作家都经历了由“前49”到“后49”的延伸,不管是来自解放区的新锐作家,还是来自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他们的创作在1949前后都具有逻辑连续性,对于他们来说,“49”不是什么特殊的门槛,不可能把他们的创作用49强制性地割裂开来研究,似乎49之前,他们的创作就是“现代”的,而49之后他们的创作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当代”的了,将视野限制在1949年之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是不完整的。
所以,“现代”文学的学科范围要扩大。但是,这个扩大不应是无边的扩大。
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概念应当是从1917至当下的文学,而狭义的作为学科概念的“中国现代文学”则应限定于1917至1977年之间的中国文学。将其拓展到1977年有如下理由:一、是有前述周锦《中国新文学简史》之历史先例可循的;二、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之内在逻辑的――既可以显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相对开放性,又可以相对保持“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断代史的相对完成性;三、特划出1977后给“中国当代文学”,以便突出其开放性、现实性的学科特点,区别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相对封闭性、历史性。
广义地讲“中国现代文学”概念自是可以包含1917至当下的所有文学的,但是,如果引用此广义概念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定义,显然会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特性的丧失。例如扩展到1999或者2000年,形成“20世纪中国文学”范畴,这样就实际上取消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部分学者打通现当代界限,形成纵览中国新文学之宏观视野的研究课题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是以其取代“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概念,则是不科学的。原因是:一、它是一个封闭的概念,现在已经是2001年后,20世纪已经终结,它不能囊括文学(批评和历史)研究对当下文学发展的动态关注,二、过于突出“世纪”概念与中国文化背景不符,“世纪”概念是西方宗教意识的产物,“世纪初”之所以在西方具有“历史开始”的意义,是因为纪元从基督诞生始,人类将获得救赎,“世纪末”之所以有“历史终结”的意味,是因为“世纪末”人类将面临审判,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世纪”之始末并没有历史开始和终结的意味,从20世纪中国历史实际来看,1901年和2000年这两个年份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划分时代的意义;三、作为学科概念,它太过笼统,不科学。
“现代文学”学科范围要拓展,但不能无边拓展。笔者以为以1977为界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实际上“20世纪中国文学”的内部统一性不够,尤其是1977之前和之后,对其进行分割,留出一部分“开放空间”给“当代文学”,将相对封闭的、完整的一部分空间划转“现代文学”是十分必要的。
过去,我们过于拘泥于传统的“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划分,主要受到这样两个观念的影响:一、误把“现代”和“当代”当成纯粹的时间概念,进而把界定的依据定位在社会时间的断代上,例如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开始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于是乎这“新时代”也成了文学时间断代(区分现、当代文学)的依据,而并没有深究社会学意义上的“新时代”和文学意义上的“新时代”是否真的对应;二、因为和“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实际流程过于接近,缺乏远距离审视的可能,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缺乏本质上的真切界定,因而只是权宜性地对两者进行了“时段性”划分,尚不能从逻辑上对二者进行更深入的界定。
三、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范围需要扩展,那么相应地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范围需要收缩。
“新时期”,这个概念用到现在多少有点儿尴尬,从刘心武发表《班主任》的1977年开始算起到现在,新时期已经延续了20余年的时间,这个“新”,似乎也太长了点。“新时期”以来,中国新文学迎来了五四以后的第2次新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丰收极大地提升了汉语言文学的创作水平,随着汉语言文学作品在国际上赢得最高大奖,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获得了在对等水平上和世界文学对话的地位,而这正是“新时期文学”的功劳。从这个角度讲,“新时期”文学值得学术界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经历来正视,然而,这些都不是在“新时期文学”这个具有强烈的批评色彩的概念烛照下可以达成的,我们必须寻找更有历史感,更有学科意义的概念来呼应它,而“当代文学”正合此一要求。
总的说来,“当代文学”是一个在时间上开放的概念,从1949年算起到现在,已经有50余年之久,相比较于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历史,它已经长了很多,似乎显得有点儿太长了。如果不适时地调整其学科范围,任“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无限地延伸、扩展下去,这对于一门学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更重要的是,以1977年为界,1949至1977年之间的“当代文学”实际上和“新时期文学”的联系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那么紧密,相反1949至1977年之间的文学大致可以划归“五四文学”“发生-发展-落潮”三阶段之第三阶段,完全可以划归“中国现代文学”范畴。目前的以49为界的“当代文学”概念是不合理的,它是把77前和77后两种不种文学形态硬行捏合在一起。
实际上,“現” 在汉语中是形声字(从玉,见声),本义为“出现”,《广韵》解“俗见字”,可见其有“明显看得见(become visible;appear;show)”、“当下呈示”的意思,现代汉语中依“现”字组的词如“现弄(在人面前炫示自己)”、“现示(显示)”、“现在”、“现案”、“现场”、“现时”、“现实”等均从本义。类推可见“现代”一词也应如此,的确,据《高级汉语大辞典》解释“现代”(modern times;the contemporary age)意为“现在这个时代(中国多指 1919 年至现在)”,“现代人”意为“当今时代的人”,“在我国历史上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后的人”。如果按此辞典义解释,“中国现代文学”应当是指“‘五四’运动以后直到当今时代的文学”。显然现行大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主流认识与此不符;从回复“现代”一词的辞典本义角度讲,“现代文学”学科范围有“拓展至49年以后”的词义学要求。
其次,从“‘五四’启蒙文学发生、发展、式微”之历史逻辑的完整性来讲“中国现代文学”有拓展到1977之后的逻辑要求。1917(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年到1977年(刘心武《班主任》发表),对于五四文学传统来说正好经历了一个发生、发展、式微的过程,以五四启蒙文学精神为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可以认为是正好完成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完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形态。而1977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在逻辑上已经不是“五四文学”一脉的了,如果说“五四文学”可以用“以民主、科学、国家为本位启蒙文学”来概括其精神的话,那么1977年以后的文学则可以用“以自由、感性、个体为本位的新感性文学”来概括其精神,当初诸多论者以“五四文学的回归”论为1977后文学张本,这种做法在那个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它可以让人们更容易地理解1977后文学,接受1977后文学的合法性,但是,现在再把1977后文学和1977前文学混为一谈,把它看成是“五四文学的回归”,显然是低估了1977后文学的价值,不利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以及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
“当”,就其时间向度的词义学内含讲,有三重涵义:一、past,刚刚过去的一个时间段,但强调这个时间段是延续到现时的,如当朝、当世;二,just at a time,指过去的某个时段,但强调的是那个时段中事件的即刻性、发生性以及与当下的关系,如当场、当初;三、present,从当前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时间段,强调该时间段的未完成性、未来性,如当前、当今。
就此,所谓“中国当代文学”,就其词义学意义而言,应当在这样几个意义上被运用:a、如果它是指“过去某个时间点到当下的”的文学,那么它的着眼点应当是强调“这个时间段的文学正在当前延续着,与当下的文学直接联系并发生着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它强调该时间段的文学与当下文学的直接连续性;b、如果它是指“从当前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时间段的文学”,那么它一定是在强调这个时间段的文学的“正在发生性”;c、如果它是指“从现在开始延续到未来的文学”,那么它应当强调的是这个文学时段的“未来性”、“前瞻性”、“开放性”。
实际上它应当在上述三个意义上同时被强调。就此,“当代文学”学科概念应当在上述三重意义上不断被调整和重新界定就是必然的:向上溯它应当不断地割舍,不断弃掉“与当下文学缺乏的直接连续性”的文学,而不断地强化它的a涵义;向下伸它应当不断地拓展自己的领地,以便能永远地保持它的c属性;就其学科的根本属性讲,它应当不断地强调自己的“现场性”,也即时刻保持其b涵义。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文学”调整其学科范围,不断割舍其前端,不断下探其末端,以便更好地体现当下现场性、未来开放性、现时回溯性,并非什么不可理解之举,而恰恰是它作为一门学科的内在规定性使然的。
1977年之后,“新时期”兴起了“新感性文学”浪潮,新的时代条件――政治上的改革、开放,经济上的市场经济化,文化上的全球化――这些都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前提,换而言之,也只有由这些要素规约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如何体现自身作为世界先进文学之属性”的问题才是具有中国文学“当代性”的问题。1949至1977年间,中国文学所处理的基本问题实际上都是“前当代”的由“中国现代”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文学如何符合无产阶级性?”的问题便是我党作为革命党在现代历史上所要处理的基本文学命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渐渐地由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肩负阶级革命之现代历史使命的革命党调整为代表全民利益的执政党,2001年江泽民“7·1讲话”便是这一转变的理论总结,文学就此也获得了其不同于“革命党”时期之核心命题的“当代核心命题”――“如何代表世界先进文化?”的问题。如果我们问:“中国当代文学不同于现代文学的基本问题在哪里(中国文学的当代性在哪里)?”其回答一定是在这里,而这一点,是1977后才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在市场化、全球化、个体化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上展开,从1977年起这个以新启蒙为核心的文学浪潮一直维持着它螺旋式发展的势头直至当下,并且获得了它而“以自由、感性、个体为本位”的内在新感性精神本质。
据此,我们说,将1977年后文学划归“当代文学”范畴是有理由的。这样做可以让“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获得它内在的精神的逻辑的统一性,进而解决当下绝大多数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所遇到的困境:这些文学史大多是生硬地糅合“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三大块,因为无法把“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没有整合性的逻辑构架,这些文学史著作常常显得缺乏“体系”,这是生硬地坚持“49”作为现当代文学学科范围界限的结果(陈思和先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6]用“潜在写作”的概念将“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在逻辑上整合了起来,可说是一种富有智慧的解决方案,但是这又造成“潜在写作”在原生态文学史中实际的地位、作用和其在叙述态文学史中地位、作用的脱离,并进而造成叙述态文学史对原生态文学的偏离)。
另外,从学科分量上讲,1977后的中国文学其实力完全可以撑起一个学科,在这个时间段,中国汉语言文学真正地获得了自己的具有“当代性”的典范作品和作家,张承志、贾平凹、莫言、苏童、余华、高行健、李锐、王安忆等在这个时间段均完成了他们的代表作,使汉语言文学真正地达到了和世界文学对话的水平。
由“中国新文学”概念的演化而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由“新时期文学”概念的演化而终有“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概念的定型,比照“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概念的成型和演化,“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范围之定型于“新时期文学”完全是符合“中国现代文学”之学科成型的历史经验的。尊重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学科分野,寻求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新世纪的历史性转型,要求我们既维护两个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反对“取消论”,同时我们又要反对“不变论”,以新观念促其新发展。重视文学研究的当下介入性、现实针对性要求我们重视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因此从“延伸到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列出“新时期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以强调之,是完全必要的。
注释: [1] 此一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诞生期,主要著作有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亚东图书馆,1924年11月)、周作人的《新文学的源流》(人文书店,1932年9月)、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华书局,1929年4月)、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等。
[2]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见《文艺论丛》第14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
[3] 此一时期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9月出上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8月出下卷)、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11月)、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等。
当代文学概念篇3
范畴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一直为学界所重。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大量具体范畴研究的基础上,很多学者开始尝试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建构。[i]范畴体系研究乃是对古代文论范畴的一种整体把握,与范畴个案研究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它需要研究者对“何为范畴”、“何为古代文论范畴”、“如何确定古代文论范畴”等前提性问题有更为自觉的认识。在已有研究论著中,很多学者对“范畴”本身做了不同程度的辨析,问题涉及“范畴”一词的涵义以及“范畴”与“概念”、“术语”之间的关系等。从其用心看,研究者显然是希望将自己对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明晰、可靠的学理基础之上;但是从实际效果看,与其说解决了一些问题,不如说暴露了更多问题。沿着这些问题追溯下去便会发现,其根源正在于未能对“范畴”以及“范畴”与“概念”、“术语”的关系获得正确的理解。鉴于此,本文拟对“范畴”问题作一番追根溯源之论,以期能提示古代文论范畴研究走出无法确定其研究对象的困境。
一、“范畴”何谓:欲辨还乱的古代文论“范畴”
说到“范畴”一词的涵义,研究者经常会引用列宁的话加以解释,即范畴是“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ii]但是,一旦进入具体操作阶段,面对古代文论中历代累积起来的无数名词术语的时候,人们又大多心生疑惑:难道这么多名词都是古代文论范畴吗?难道这么多名词都需要我们联结到古代文论的体系之网中去吗?而人们的直觉反应往往是:这不太可能!于是由疑惑而生否定,人们便希望能够分清这些名词中哪些才是“真正”的文论范畴,哪些则不是。那么,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呢?那些不能归入文论范畴的词语又该称为什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者引入了“概念”和“术语”,试图以“术语-概念-范畴”三分模式为框架,将“真正”的文论范畴甄别出来,而将剩下的文论词语分别划归“术语”和“概念”之内。
汪涌豪先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一书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关系的辨析在有关论著中颇有代表性。对于“范畴”与“概念”的关系,他认为,“范畴是比概念更高级的形式”,[iii]“概念是对各类事物性质和规律关系的反映,是关于一个对象的单一名言,而范畴则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名言,是关于一类对象的那种概念,它的外延比前者更宽,概括性更大,统摄一连串层次不同的概念,具有最普遍的认识意义。”[iv]并举例说明,“范畴指超越于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一些理性规定。譬如‘格律’之和谐、精整,‘结体’之遒劲、疏朗,这‘和谐’、‘精整’、‘遒劲’、‘疏朗’是概念、范畴,而‘格律’、‘结体’则不是。”[v]对“概念”与“术语”的关系,他认为,“术语是指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上述‘格律’、‘章法’属此,其情形正同‘色彩’之于绘画,‘飞白’之于书法。概念和范畴则不同,概念指那些反映事物属性的特殊称名,与术语一旦形成必能稳定下来不同,它有不断加强自己的冲动,它的规范现实的标准越精确,意味着思维对客体的理性抽象越精确。”[vi]据此他批评“有人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范畴作泛化处理,在确认‘道’、‘气’等本原性范畴,‘神思’、‘兴会’等创作论范畴,‘靡丽’、‘豪放’等风格论范畴之外,还将‘格律’、‘结字’、‘章法’、‘流别’、‘文风’等也定性为范畴,从而使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线索,因此显得淆乱不清。”[vii]但是看过论者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关系不可谓不详细的分析,却很难让人有明朗、清晰之感。其中的很多论断乍看很像那么回事,倘若细究,则又显得游移不定。例如,论者认为“概念”是“关于一个对象的单一名言”,而“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名言”。后一句也许没有问题,但是说“概念”只与“一个对象”有关则明显与事实不符。现实中不仅有指称一个对象的概念(如“长城”、“故宫”等),更有不少概括很多对象的概念(如“人”、“马”等)。显然,以反映对象的“单一”和“普遍”作为区分“概念”和“范畴”的标准是很不可靠的。那么,如若以所反映对象普遍性程度的高低来区分“概念”和“范畴”又是否可行呢?这样做同样会面临诸如“究竟所反映对象的普遍性高到何种程度才是范畴,低到何种程度才是概念”之类的困惑。再如,论者认为“范畴”不应该是“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而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一些理性规定”,认为“格律”、“结体”等表示文章构成和创作技巧的名词仅仅是文论的“术语”,而只有那些表示“格律”、“结体”特征的词语如“和谐”、“精整”、“遒劲”、“疏朗”才是概念和范畴。这种说法问题更多:难道一门学科的专门术语就仅仅是那些“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名言?难道“格律”、“结体”是古代文论的“术语”,而“和谐”、“精整”等就不能是古代文论的“术语”?难道一个词语是“术语”的同时就不能是“概念”和“范畴”?反之,难道一个词语是“概念”和“范畴”的同时就不能是“术语”?而最令人疑惑的是,论者在这里反对把“章法”列为范畴,但是在该书后面论述古代文论范畴系列时,“章法”又被明确视为创作论范畴,而且与之一起被列入创作论范畴的还有“字法”、“句法”、“构思”等众多属于“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viii]这岂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
罗宗强先生对术语、概念和范畴关系的看法比较审慎。他认为解读古代文论范畴是“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领域,哪些属于范畴,哪些只是一般的批评辞语?哪些是常用的、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古文论系统,哪些只是用于一时,带着随意的性质?因了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对于范畴的选择标准也就不同。有的学者已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意见。但要取得普遍的认同似尚须一个较长的讨论过程。例如,我们如果把‘奇’作为一个范畴,那么与之相类的‘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飘逸’等等就应该归入范畴之列;同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很大一部份,也都应该归入范畴之列。那么它们是不是范畴呢?要知道这类用语是很多的,多到可能有上百个,而且其中的不少是带着随意性的,并不普遍也不经常被使用。它们中的一部份,甚至只是某一位评论者在某一次的随意的评论中用过。他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既未作认真的概念内涵的严格界定,事后也未曾有意义连贯的使用。我们是称这一些为术语呢?还是称它们为概念?还是称它们为范畴呢?那么我们要在这些性质不易界定的术语、概念、范畴中挑选哪些作为范畴的研究对象呢?另外一些词语如‘诗言志’、‘诗缘情’、‘文明道’等等,也有研究者把它们当成范畴。它们究竟是不是范畴?实在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文论短语,当作一个完整的文学观点?面对古文论上的这些复杂现象,我们有时可以从纯粹理论上为‘范畴’一词下定义,来决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但一到具体问题,立刻就会遇到麻烦。正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有的研究者在面对这类问题时常有不易驾驭之感。例如,同一部著作中对同一个词前称概念后称范畴,或者理论阐述时把概念与范畴区别开来,而具体论述时又把二者含糊放在一起。我们似乎可以说,百年来的范畴研究,似是在一种概念尚模糊、理论认识尚未十分明晰的状态之下展开的。”[ix]
之所以将罗先生的这段原文照引,并非因为这段话提供了问题的答案,而是因为它指出了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中国近百年来几代人所做的古代文论范畴的现代研究,基本上“是在一种概念尚模糊、理论认识尚未十分明晰的状态之下展开的”。尽管罗先生本人也没有明确提出确定古代文论范畴的统一标准,但从他对学界有关古代文论范畴认识的模糊性的具体评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他的大致思路:第一,一个文论用语是否属于范畴应该与这个用语使用的普遍性有关;第二,古代文论用语应该根据其使用情况分为术语、概念和范畴,作为范畴的文论用语应该与作为术语和概念的文论用语有所区别;第三,还应该在古代文论中的概念和范畴的外延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同一个古代文论用语不宜既称为概念又称为范畴。罗宗强先生的观点与前述汪涌豪先生的看法大体相同,也反映了很多古代文论范畴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其核心是试图将古代文论用语明确划分为“术语”、“概念”和“范畴”三类而不相“混淆”。但是,论者自身的矛盾已经表明,这一试图消除古代文论范畴“混淆”的方法非但未能真正消除古代文论范畴的“混淆”,反而造成了更明显的混乱。
那么,走出困境的出路在哪里呢?
二、“范畴”探源:亚理士多德的“范畴论”
问题的症结恰在于研究者未能真正理清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区别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内涵的同时,也对其外延做出了过于机械的划分。
所谓术语(Term),诚如汪涌豪先生所说,是指“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也可称各门学科中的专门名词(广义的);而中国古代文论术语,当指中国古代文论这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或名词。由此可知,古代文论术语是针对古代文论这门学科而言的,指的是具有古代文论学科特点的那些名词;因此,确定有关论著中的某个用语是否属古代文论术语,主要是看这一用语是否具有古代文论学科的特点,也即是看这个用语是否是对有关文章问题的描述和规定。古代文论术语的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其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理应包括古人有关文章的起源(如“道”、“气”、“圣”等)、创作(“格律”、“结体”、“章法”)、文本(如“文质”、“意象”、“意境”、“神韵”、“和谐”、“精整”、等)、欣赏(如“知音”、“滋味”、“兴”等)、发展(如“通变”、“源流”、“体用”等)等各种问题的论述中所使用的众多词语。而且,所谓术语的“学科特点”并不意味着不同学科术语之间的对立,同一个用语既可以是此一学科的术语,也可以是彼一学科的术语,如“道”、“气”、“神”、“理”、“性”、“情”等,可以同时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正因此,确定古代文论术语的关键是根据这个词与古代文论学科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根据这个词与其他学科用语之间的外部关系。
概念(Concept)是关于某种事物的观念,表现为语言中的词。概念与词虽然有观念与符号之别,但二者是一里一表的关系,当我们思及某个概念时总是要想到某个词,而当我们说到某个词时,也总是意味着在表达某个概念。古代文论的概念是古人关于文章的观念,其具体表现即为古代文论中的描述、说明和规定文章的众多词语。这也就是说,并非古代文论著作中的所有词语都是古代文论的概念,前提条件是这个词必须表示有关文章的某种观念和思想。据此不难想像,古代文论的概念同样是非常丰富的,它应当包括古代文论中所有有关文章发生、发展、创作、构成、特征、接受等各个方面的观念,无论这个观念是主体的还是对象的,是整体的还是部分的,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范畴(Category)与术语、概念一样都是西语译词,但较之术语和概念,范畴的涵义稍显复杂。作为认识论和逻辑学用语的“范畴”一词始于亚理士多德的《工具论·范畴篇》。在《范畴篇》中,亚理士多德把语言的表达形式分为“复合的”和“简单的”两种,复合的表达如“人跑”,“人得胜”,简单的表达如“人”、“跑”、“得胜”等。按照现在的说法,“复合的”表达相当于或长或短的句子,“简单的”表达则相当于词。亚理士多德又将“一切非复合词”(即“简单的表达”,也即词)分为“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和“遭受”10类,并举例说明:“实体,如人和马;数量,如‘两肘长’、‘三肘长’;性质,如‘白色的’、‘有教养的’;关系,如‘一半’、‘二倍’、‘大于’;地点,如‘在吕克昂’、‘在市场’;时间,如‘昨天’、‘去年’;姿态,如‘躺着’、‘坐着’;状况,如‘穿鞋的’、‘贯甲的’;活动,如‘分割’、‘点燃’;遭受,如‘被分割’、‘被点燃’。” [x]亚理士多德把这10类“非复合词”称之为10类κατηγοριαs,汉语把这个词翻译为“范畴”,取《尚书·洪范》“洪范九畴”中的“范”“畴”二字组合而成。“洪范九畴”中的“范”意为方式、方法,“畴”意为同类、类别,合为“范畴”有“方法的类型”之义。但是,作为“方法类型”的“范畴”一词主要反映的是由古希腊语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衍生而来的category(英语)一词的若干现代用义之一,严格地说,并不能准确传达出亚理士多德所使用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原初内涵。
Κατηγοριαs是亚理士多德在著《范畴篇》时自撰的一个词语,衍生自另一个非常普通的古希腊惯用语κατηγορειν。Κατηγορειν在古希腊语中意为“反对某人的言说”、“控诉”,其本身又由κατα与αγορενειν两个部分构成。Κατα是古希腊语中一个普通的介词,意为“使……向下”,αγορενειν意为证明或公开地说,合为κατηγορειν一词,便可表示“控诉”、“反对之语”等义。一般说来,“控诉”(κατηγορειν)总是意味着要运用言语对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和说明,而这也应该是亚理士多德依此创造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基本用义。换言之,亚理士多德把表示“实体”、“性质”、“关系”、“数量”等10类词称为κατηγοριαs,即意在表明它们都是从某个方面描述、说明事物的词。亚理士多德在除κατηγοριαs之外,还经常使用与此相近的含有“肯定”、“说明”之义的κατηγορεισθαι一词,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所造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主要用义。综合这些分析,亚理士多德在《范畴篇》使用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更适合译作“谓词”——“谓”意为说明,“谓词”即用于说明之词。[xi]
根据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基本内涵和亚理士多德对κατηγοριαs的具体论述,可以对其“范畴论”做出两个最基本的说明。第一,亚理士多德“范畴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即是广泛存在的所有的词(“一切非复合词”),这些词是用来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第二,根据词描述、说明事物的不同角度和层面,亚理士多德把所有的词归入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类,并把这10类词统一称为“谓词”(范畴)。因此第三,汉语学界所说的亚理士多德的“范畴论”实为“谓词论”,所谓10类“范畴”即10类“谓词”,也即10类说明事物之词。
分析至此,便接近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的具体所指(即外延)究竟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仅仅是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个概念(词)。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可称为“谓词”(范畴)的概念(词)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与亚理士多德的本义不符。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的具体所指可以分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先,从其最直接的用意看,“谓词”(范畴)应是指包涵在这10类“谓词”(范畴)中的所有具体的词,也即用于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一切非复合词”。亚理士多德的逻辑其实很清楚:所有的词可以分为10类,这10类词即是10类“谓词”(范畴),因此其中的每个词也自然都是“谓词”(范畴)。详言之,每个词从其所在的“谓词”(范畴)类别看,可称为“某某谓词”(某某范畴);而从其所在的类都是“谓词”(范畴)的一类看,每个词又可以直接统称为“谓词”(范畴)。例如,我们一旦确定“黑”、“白”、“好”、“坏”等词属于“性质谓词”(性质范畴),那么它们也就毫无疑问地都是“谓词”(范畴)。“谓词”(范畴)与每个具体的词的关系乃是共名与个体的关系——共名总是适合于每一个个体,正如“人”这个共名可以用来泛称每一个具体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的直接所指是极其广泛的,实际上包涵了所有用来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词。这一结论也许会让一些研究者颇感意外,但这又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本身即意为“用于说明之词”,而事实上又有哪一个词不是“用于说明(事物)”的?[xii]其次,既然“谓词”(范畴)的本义是指所有用于说明事物之词,那么据此可以认为那些表示各类“谓词”(范畴)名称的词本身如“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个词也同样应该属于“谓词”(范畴)。具体地说,这10个词所说明的是第一层意义上的10类众多的具体“谓词”(范畴),例如,“人”、“两肘长”、“白”、“一倍”等词是用来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具体“谓词”(范畴),而“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等又是用来描述、说明“人”、“两肘长”、“白”、“一倍”等具体“谓词”(范畴)的“谓词”(范畴)。——这可以视为亚理士多德所说“谓词”(范畴)的第二层所指。沿着这一思路还可以追问:作为所有具体“谓词”(范畴)总名的“谓词”(范畴)本身是否也是一个“谓词”(范畴)?答案自然也是肯定的,因为“谓词”(范畴)这个词其实是对“一切非复合词”的一个总的描述和说明。——这可以视为亚理士多德所说“谓词”(范畴)的第三层所指。
如果说第一层次的具体所指是亚理士多德《范畴篇》“谓词”(范畴)的“实谓”(即《范畴篇》“谓词”(范畴)的实际所指),那么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具体所指则是亚理士多德《范畴篇》“谓词”(范畴)的“当谓”(即根据《范畴篇》之理,其“谓词”应当有的具体所指)。但无论是哪个层次的“谓词”(范畴),就其都是说明事物的“谓词”(范畴)而言,其间并没有根本差异。由此可见,根据亚理士多德“谓词论”(范畴论),语言中所有的词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说明某种事物的“谓词”(范畴)。
三、“范畴”涵义辨析及“范畴”、“概念”、“术语”关系另解
藉由对亚理士多德《范畴篇》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对其“范畴论”形成以下几点基本看法:第一,“范畴”实为“谓词”,即用于说明事物之词。这是“范畴”一词的原初内涵,也是作为认识论和逻辑学术语的“范畴”一词的基本涵义。认识到这一点可防止对“范畴”(category)一词不同用义的混淆。我们知道,在现代西语中,“范畴”一词经常用来表示某些基本的、明确区分的实体类别或概念类别。笔者暂未找到有关语言学资料,可以清楚地说明最初表示“说明事物之词”的“范畴”究竟是如何在现代西语中衍生出了“事物类别”(包括“概念类别”)这一流传甚广的用义,但是下面的这个推理应该有一定的道理。根据前文分析,在亚理士多德的《范畴篇》中,“范畴”一词是10类“非复合词”的共名,10类“非复合词”即10类“范畴”,或者说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范畴”包涵了10类“非复合词”;又因为词是概念的表现形式,所以也可以认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范畴”包涵了10类概念。但是在后人的理解中,“范畴”由表示“10种类别的概念”逐渐变成了表示“10种概念的类别”,这样“范畴”也就有了“概念的类别”之义。在“概念类别”这一用义的基础上再稍作引申,“范畴”便有了“事物类别”这一更广泛的用义。这一衍变过程可以示意如下:
各类“非复合词”——各类概念——概念类别——事物类别
可以看出,在“范畴”一词用义的整个衍变过程中,从表示“各类概念”到表示“概念类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有人可能认为,“范畴”表示“各类概念”与表示“概念类别”,其间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但事实并非如此,二者表示的实际意义区别甚大:说“范畴”表示“各类概念”,表明这是用“概念”来说明、界定“范畴”,“范畴”与“概念”之间是种概念和属概念的关系,表明“范畴”本身也是“概念”,最终要表现为具体的“概念”。这个意义上的“范畴”,其具体所指应该是各类概念中的所有具体的概念(词),如《范畴篇》中的“范畴”即应该是指“人”、“两肘长”、“白”、“一倍”等所有具体的词。但如果说“范畴”表示“概念类别”,则是用“类别”来界定、说明“范畴”,视“范畴”为一种“类别”。这种意义上的“范畴”,其具体所指则是这些概念的“类别”,而不是所有具体的概念。照此理解,《范畴篇》中的“范畴”就只能是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等词所指称的10类“非复合词”的“类别”本身,而不是各类中所有具体的词——“词的类别”与“各类具体的词”的区别正如“人类”与“各类具体的人”的区别,其实质是类别与个体的区别,二者虽极易混淆却又绝不能混淆。
上述分析也表明,当人们不再把亚理士多德的“范畴”理解为“各类概念”的共名而是理解为“概念类别”的共名时,其实已经背离了“范畴”一词的原初用义。但是在西语中,“范畴”一词的原初涵义与现代用义是并存的,学者一般也能够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和适用语境。问题是,当我们组合成“范畴”这个汉语词把κατηγοριαs 以及其他语言中与之相应的category等词翻译为汉语时,却只能表达出这个词所表示的“概念类别”或“事物类别”这层用义,而将其对学科“范畴”研究而言极为重要的“谓词”这一本义遗落了。这一表意并不完整的翻译埋下了汉语学界学科范畴研究中乱象丛生的病根。正是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了对各种学科理论范畴的具体所指的普遍误解,主要表现为仅仅把作为各类概念的名称的词当作“范畴”,同时把各类概念中的具体概念仅仅视为“概念”以便与其所理解的“范畴”区别开来。如认为亚理士多德《范畴篇》所说的“范畴”仅是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个作为10类词名称的词,而不是指这10类词中所包涵的“人”、“两肘长”、“白”、“一倍”等众多具体的词。论者并没有认识到,亚理士多德实际上是把“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这十类词称为“范畴”,而不是仅仅把“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这十个词称为“范畴”(当然,这十个词对其所说明的这十类词来说也是范畴,但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的范畴)。转贴于
第二,“范畴”作为说明事物之词总是针对其所说明的事物或事物的某个方面而言的,当一个词被用于说明某个事物或事物的某个方面时,这个词也就成了说明某个事物或事物某个方面的某类“范畴”中一个。如当我们用“相同”这个词说明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时,“相同”也就成了说明这两个事物关系的一个“关系范畴”。从原则上说,一切语言中的一切词都可用于说明事物,因此一切语言中的一切词在一定条件下都会成为“范畴”。“范畴”与词的这层关系,为我们提供了确定某个学科或某个理论的“范畴”的明确标准:所谓某个学科或某个理论的“范畴”,也就是所有用以从某个方面描述、说明这门学科或这一理论研究对象的词(概念)。这些词就其所描述、说明的研究对象的某个方面而言,可称为“某类范畴”;而就其所描述、说明的整个研究对象而言,又可统称为“某学科范畴”或“某理论范畴”。
第三,既然“范畴”即是用以从某个方面说明事物的词(概念),那么根据所说明事物的范围大小不同,作为“范畴”的词的数量也会有多少之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有关“范畴论”可以根据其所说明的事物范围的大小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即“一般范畴论”和“学科范畴论”。所谓“一般范畴论”就是关于说明所有事物的所有的词的理论。前述亚理士多德的《范畴篇》即属于这一层次的范畴论。《范畴篇》并不研究某一具体学科、具体理论的范畴,而是从超越具体学科和具体理论的最一般的层面,把语言中所有用于说明各种事物的词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并在所有的词与作为整体存在的世间各种事物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说明与被说明的关系。这是一种关于范畴自身的“范畴论”,它虽然并不深入研究世界上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但一切事物却都是其观照的对象;虽然并不精心分析语言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词,但所有的词却都是其关注的目标。作为“一般范畴论”,既然它所研究的是用于说明所有事物的所有的词,因此在它这里所有的词就是关于所有事物的范畴,词与范畴实现了完全的统一。亚理士多德又把所有的范畴分为10个基本的大类,这是对“一般范畴”更深入的说明。
所谓“学科范畴论”是指有关某一具体学科和某一具体理论的范畴的理论,诸如“哲学范畴论”、“社会学范畴论”、“诗学范畴论”等。“一般范畴论”与“学科范畴论”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一般范畴论”揭示的各种“学科范畴论”共同蕴涵的一般性规律,而各种“学科范畴论”则是一般性范畴规律的具体体现。“学科范畴论”与“一般范畴论”的主要区别在于:“一般范畴论”中的范畴说明的是语言所能反映的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而“学科范畴论”中的范畴说明的则是作为某一具体学科研究对象的某种或某类事物;前者的外延(在理论上)是泛指的、无限的,后者的外延则是特定的、有限的。
至此,我们已经对术语、概念、范畴三者作了必要的分析和比较。简言之,术语是指一门学科的专用名词,概念是指关于事物的观念,范畴则是指(从不同方面)说明某个事物的词(概念)。显然,如果单从内涵上看,三者具有各自的独特规定性;但是如果从某个特定学科的术语、概念、范畴三者的外延上看,就会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个特定学科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在外延上是基本一致的。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作为这个特定学科专用名词的“术语”,实即是从各个方面说明、描述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各种词语;而作为这一特定学科的“概念”,包涵了关于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的观念,其表现形式也是那些从各个方面说明、描述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各种词语;至于这一学科的“范畴”,同样是从各个方面说明、描述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这些词语。也即是说,同一个词,从其作为说明这个学科研究对象的一个用语来说,可称为这一学科的“术语”;从其所反映的有关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观念来说,则可称为这一学科的“概念”;而从其作为从某个方面说明这个学科研究对象的某类概念中的一个概念来说,又可称为这一学科的“范畴”。即以“韵味”这个词为例,它是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一个专用名词,因此可称为“古代文论术语”;它又反映了古人关于文学作品性质的一种观念,因此又可称为“古代文论概念”;它还是古代文论中用以说明文学作品性质的一类概念中的一个,因此还可称为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作品性质的范畴”。总之,在同一学科中,术语、概念和范畴是三位一体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实际上是对这一学科理论所包涵的、具有这一学科理论特点的、用于描述规定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有关词语的不同命名,表示的是同一个词在不同关系中的三种不同的身份。
当然,还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同一个词作为概念和作为范畴的区别。当我们称一个词为“概念”时,意在表明它反映的是某个事物或事物某个方面的观念,强调的是这个词与其反映的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当我们称这个词为“范畴”时,则意在表明它表示有关某个事物的各类概念中的一个具体概念,强调的是这个词(概念)在有关这个事物的所有概念所构成的概念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和位置,也即是强调这个词(概念)与其所处的概念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走出古代文论范畴研究的困境
当我们理解了术语、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这层关系,重新回到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这个话题时,很多缠夹便能够厘清,许多误解便可以消除。首先,我们在确定古代文论范畴的具体所指时不会再陷入非此即彼的机械困境,而是遵循亦此亦彼的辨证思路。我们不必再为古代文论中的某个词语究竟是“术语”还是“概念”抑或是“范畴”大费其神,因为它既可以是术语,也可以是概念或范畴。如前引汪涌豪先生所举“章法”一词,本是术语、概念、范畴三位一体,论者的错误并不在于既称其为术语(前),又称其为范畴(后),而在于一面坚持对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外延作机械划分,一面在具体研究中又无法严格遵循这一划分。这一自相矛盾恰恰说明,在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外延之间进行机械划分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其次,我们也不必再因为误解范畴的“普遍性”而陷于对“哪些古代文论用语是普遍使用的范畴,哪些古代文论用语仅仅是随意性使用的概念”之类问题的困惑。确定某个概念是否属于范畴,其标准并不是看这个概念的使用是普遍还是随意,而是根据这个概念是否是从某个方面对有关研究对象(实体)的规定和说明。根据这个标准,无论是使用极广的“赋”、“比”、“兴”、“意境”、“意象”、“境”、“气”、“风骨”等,还是使用范围较小、时间较短的概念,甚至只是个别人使用的概念(如扬雄论文所用的“元”、“妙”、“包”、“要”、“文”,明唐顺之论文所说的“丹头”等[xiii]),从有关文章的某个类别的概念来看都可以称为古代文论的范畴(如扬雄所说“元”、“妙”、“包”、“要”、“文”等是说明文章特征的范畴,唐顺之所说的“丹头”是说明文章构成的范畴)。学界因循的根据概念使用的普遍性确定何者为范畴的做法,不惟与概念和范畴的辩证关系不合,亦且带有很强的经验性,以至于反复陷入其本来要竭力避免的随意性。第三,不至于再将不同范畴层次间的区分与概念和范畴的区分相互混淆。如薛富兴先生曾在《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一文称:“范畴是反映一门学科研究对象和过程最重要环节,勾勒该学科基本轮廓的核心概念,是一门学科的骨架。反映每一门学科体系的范畴的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但每一个范畴却可以有不同的概念表达形式。”[xiv]其实“反映一门学科研究对象和过程最重要环节,勾勒该学科基本轮廓的核心概念,是一门学科的骨架”以及“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云云,说的并不是一门学科所有范畴的特征,而应该是这门学科的“基本范畴”或“重要范畴”的特征。而一门学科中除了这些基本范畴和重要范畴外,还有大量的“非基本范畴”和“次要范畴”,这些范畴却并不一定要“反映一门学科研究对象和过程最重要环节”,也不必“是一门学科的骨架”,其数量也不是“十分有限”,而应该是“十分丰富”的。例如,在他所举的“味”与“滋味”、“韵味”、“兴味”等文论名词中,并不能因为“味”是“滋味”、“韵味”、“兴味”等概念的共名,就认为只有“味”是“范畴”,而“滋味”、“韵味”、“兴味”等就只是“概念”。一个恰当的说法是:“味”是一个文章鉴赏范畴,而“滋味”、“韵味”、“兴味”等则属于文章鉴赏范畴中的“味”一类范畴。在古代文论范畴中,“味”所处的范畴层次可能稍高一点,而“滋味”、“韵味”、“兴味”等所处的范畴层次可能稍低一点,但这却并不等同于范畴与概念的区别。事实上,如果仅仅根据“味”与其所表示的某个文章鉴赏观念的关系,那么“味”一样可称为“概念”;而如果着眼于“滋味”、“韵味”、“兴味”等与有关文章鉴赏的这类概念的关系,那么它们同样可以称为“范畴”。[xv]
理解了术语、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这层关系,前引罗宗强先生的一系列疑问也便可以得到解释。如问:“我们如果把‘奇’作为一个范畴,那么与之相类的‘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飘逸’等等就应该归入范畴之列;同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很大一部份,也都应该归入范畴之列。那么它们是不是范畴呢?要知道这类用语是很多的,多到可能有上百个,而且其中的不少是带着随意性的,并不普遍也不经常被使用。它们中的一部份,甚至只是某一位评论者在某一次的随意的评论中用过。”本文的回答是:“奇”与“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飘逸”等都毫无例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说的那些词语也同样应该归入古代文论范畴之列;不论这类用语多到何种程度,也不论其使用带着多大的随意性和不普遍,按理都应该是古代文论的范畴。只要是古人从某个方面描述、规定文章的词语,都属于某种类型的古代文论范畴(罗宗强先生列举的这些用语属于“文章特征范畴”或“文章风格范畴”)。又问:“我们是称这一些为术语呢?还是称它们为概念?还是称它们为范畴呢?那么我们要在这些性质不易界定的术语、概念、范畴中挑选哪些作为范畴的研究对象呢?”本文的回答是:我们既可以称这些词为“术语”,也可以称这些词为“概念”和“范畴”。由于这些词都可以称为范畴,所以也就不必在它们中挑选哪些作为范畴的研究对象,我们要做的是确定哪些范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哪些范畴作为次要研究对象。至于罗宗强先生所说的“同一部著作中对同一个词前称概念后称范畴,或者理论阐述时把概念与范畴区别开来,而具体论述时又把二者含糊放在一起”这种现象,恰恰是同一学科理论中概念与范畴的外延重合关系的真实反映。同一个文论词语,当研究者为了强调它所反映的某个文章观念时,往往会不自觉地称之为“概念”,而当研究者为了强调它与关于文章的概念系统中的某一类概念的关系时,往往又会很自然地称之为“范畴”。因此,说“任何范畴必须是概念”当然没错,但是说“并非所有的概念都是范畴”则要作具体分析:如果这是一些孤立的概念当然不是范畴,但如果这些概念都是某个学科理论中的概念,都是从不同方面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规定和说明,那么则应该都属于这一学科的某类范畴。
罗宗强先生的另一个问题也很有意义,即“诗言志”、“诗缘情”、“文明道”等究竟是不是范畴的问题。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根据亚理士多德的理解,范畴应该是“非复合词”(即词),而不应是“复合的”语言表达(即句子)。“诗言志”、“诗缘情”、“文明道”等显然并不是词语(罗宗强先生称之为“词语”是不准确的),而是短句(与亚理士多德所说的“人得胜”这一复合语属于同一类表达形式),因此不能称之为古代文论范畴——恰当的说法是“古代文论命题”。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之间关系的误解,不仅存在于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研究中;甚至可以说前者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关系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后者的影响。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这部著作。在该书中,张岱年先生对名词、概念、范畴做出了明确区分:“名词、概念、范畴三者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别性。表示普遍存在或表示事物类型的名词可称为概念,如物、马等等。而表示一个人或某一物的名词不能叫做概念,如一个人的姓名称号或某一历史事件的名称等等都不是概念。在概念之中,有些可以称为范畴,有些不是范畴。简单说来,表示存在的统一性、普遍联系和普遍准则的可以称为范畴,而一些常识性的概念如山、水、日、月、牛、马等等,不能叫做范畴。”[xvi]张岱年先生所理解的三者的关系是一种逐层包含的关系,即名词包含概念,概念又包含范畴。从外延上来看,名词的外延最大,概念的外延次之,范畴的外延最小。但是,张岱年先生的这种区分并没有足够的学理根据:如为什么只能称表示一类事物的名词为概念,而不能称为表示某个特定事物的名词为概念?事实上所有的名词都应该表示概念(亚理士多德甚至把表示“第一实体”——即不可再分的单个事物——的词归为“实体范畴”)。又如:为什么说那些“常识性的概念”如山、水、日、月、牛、马等不能叫做范畴?而在亚理士多德所划分的10类范畴中,就有一类专指“人”、“牛”、“马”、“动物”等概念(词)。亚理士多德把这类范畴称为“实体范畴”,而且是所有10类范畴中的核心范畴。
张岱年先生又根据上述思路对中国古代哲学用语做出了更具体的划分。他认为:“凡一家独用的概念或名词,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例如墨子所讲的‘三表’,在墨家思想中是很重要的,但没有被别的学派接受,墨家灭绝之后,‘三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公孙龙所谓‘指’是他一家的一个独创的概念,也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的承认的范畴。还有些概念,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颇为流行,但后来销声匿迹了,例如‘玄冥’、‘独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颇为流行,唐宋以后则无人采用,因而也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又有个别的思想家,喜欢自造生词,如扬雄在《太玄》中仿照《周易》‘元亨利贞’而独创的所谓“冈、直、蒙、酋”,只能算作个人的用语,不能列为范畴。”但他接着又说:“但是,也有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概念,虽然没有普遍流行,却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某一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所以仍可称为哲学范畴。例如张载所谓‘能’(《正蒙·乾称》:‘屈申动静终始之能’)、方以智所谓‘反因’(《东西均·反因》),似乎都可以列入古代哲学的范畴。”[xvii]前后两段对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根据所谓“普遍性”和“流行性”这一模糊的、经验的标准来确定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所带来的随机性和矛盾性。前面说“一家独用的概念或名词,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后面又认为有些思想家独创的、没有普遍流行的概念“仍可称为哲学范畴”;前面判断范畴的标准是概念使用的普遍性和流行性,后面判断范畴的标准则又变成了“较高的理论价值”。再有,说“凡一家独用的概念或名词,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又说“玄冥”、“独化”“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那么这些没有“普遍意义”的范畴究竟是不是范畴?根据一般逻辑,没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当然还是范畴;但根据论者确定范畴的标准,似乎又不能算是真正的范畴。另外,如果因为“玄冥”、“独化”在唐宋以后无人采用便不能算是范畴,那么古代很多哲学用语现在都已经不再被采用,这岂不是说它们都不能算是范畴吗?种种矛盾说明,根据所谓概念使用的普遍性和流行性来确定何者是范畴,实际上是走进了一个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怪圈,只能左支右绌,平添各种混乱。
普遍性可以作为区分普遍范畴和非普遍范畴的标准,流行性可以作为区分流行范畴与非流行范畴的标准,理论价值可以作为区分理论价值较高的范畴和理论价值较低的范畴的标准,但是它们都不能作为区分范畴和非范畴的标准。确定某个理论的范畴的标准只能是概念(词)与有关某个实体的概念系统中的某类概念的关系。具体地说,首先是看这个名词(广义的)是否是对这一理论所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规定。这是确定范畴的最基本的标准,一个词只要是对有关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规定,即使暂时不知道它究竟属于其中的哪个类别的概念,仍然可以肯定它是关于这个研究对象的理论的范畴。其次是看这个词属于有关研究对象的概念中的哪个类型。这一步是为了对这个范畴获得更具体的认识。范畴分类的角度和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分别做出不同的划分。概言之,只要是符合上述条件的词,都可以称为有关某个研究对象(实体)的某类范畴;这与其使用人数的多少无关,与其使用时间的长短无关,也与其理论价值的高低无关。
总之,术语、概念和范畴虽然内涵有别,但就某个特定的学科理论而言,其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外延是完全相同的。一旦理清了这层关系,我们在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便可以挣脱很多近似于“作茧自缚”的限制和拘束,并克服由此带来的种种方法和视野上的缺陷,使得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最为广泛、最为完整的把握成为可能。理清了这层关系,我们便不必再犹疑、困惑于究竟哪些概念(词)才是古代文论范畴之类的问题,而是把更多的心思用于区分古代文论范畴的类型与层级,辨析各类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各种范畴的基本内涵,探析各种范畴的历史源流等。当然,这已经是下一步的研究任务了。
[i] 有关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研究的主要论文有:彭修银的《关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系统化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92年第4期),党圣元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管见》(《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和《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蒲震元的《从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姜开成的《论“意象”可以成为文艺学的核心范畴》(《浙江学刊》1997年第4期),薛富兴的《关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体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李凯的《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再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牛月明的《中国文论话语的元范畴臆探》(《文史哲》2001年第3期)等。研究专著有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詹福瑞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蔡钟翔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先后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现已出版10余种),汪涌豪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ii] 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页。
[iii] 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iv] 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v] 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vi] 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vii] 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viii] 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4-570页。
[ix] 罗宗强:《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见《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罗宗强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文为该书序言。
[x] 参考《工具论·范畴篇》,秦典华译,《亚理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引用时略有改动。
[xi] 邓晓芒在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时,把德语中的pradikamente一词译为“云谓关系”,表明译者注意到了该词源自的古希腊语κατηγοριαs的原初用义。见《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著,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xii] 从《范畴篇》的具体表述也可明确看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范畴”的直接具体所指乃是各类“范畴”中的具体的词。如称:“‘相同’、‘不同’、‘相等’、‘不等’都可以使用‘更多’或‘更少’这样的字眼。这些词都属于关系范畴。”(《工具论·范畴篇》,秦典华译,《亚理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亚理士多德是把“相同”、“不同”、“相等”、“不等”这些具体的词称为“关系范畴”的。依此类推,被称为“实体范畴”、“数量范畴”等各种“范畴”的也应该是包涵其中的具体的词。统言之,这些具体的词即一个个“范畴”。
[xiii] 扬雄语见《渊鉴类函·文章》引扬雄《法言》逸文。原文为“圣人之文,其隩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又言:“幽深之谓元,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唐顺之语见明万士和《二妙集序》引。以上材料均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汪涌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xiv] 薛富兴:《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当代文学概念篇4
一、概念法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从当代国际比较法的角度看,我国民法属于大陆法系,特别是深受德国民法的影响。
德国法系和法国法系是大陆法系的两个主要支系(另一个支系是斯堪的纳维亚法系或称北欧法系),它们又被称作法典法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注重概念和法典的内在逻辑体系。这就是所谓理性主义精神。理性主义是近代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罗马法复兴运动的共同精神。
就罗马法复兴和近性主义法学思想而论,以下几个要点是重要的:(1)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即以个人的法律人格和权利、自由为法律的价值中心;(2)法律的统一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稳定性;(3)法律的概括性和逻辑性。在这些要点背后,存在着两个基本的信念:第一,法律现象的守恒性,它使人们相信,可以通过一套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一劳永逸地将各种法律现象有条不紊地纳入法律制度的调整范围;第二,法律价值的单一性,它使人们相信,现行法律秩序所维系的价值体系是唯一的和至高无上的,因而不允许成立体系外其他价值的合法性。总的来说,法典法系的宗旨,在于建立一套完整、精密和恒定的规范体系,以确保自由主义的法秩序能够普遍、稳定和永久地存续下去。
与此相适应的理性主义法律思维方法,是一种以概念为中心的方法。在法典法系中,基本的法律规范是用具有高度概括的概念来表达的。这些概念既是社会生活中具体法律现象的抽象,也是法律秩序中法律价值的载体和法律目的的代表。同时,概念也是联结整个体系结构,实现法律规范整合的媒介和纽带。所以,在法律运行过程中,规范地理解、解释和应用,都必须借助概念,甚至依靠概念。
这种以概念为中心的法律思维方法,就是所谓的概念法学。在本世纪前半期,以民法总则为代表的德国民法典模式及其概念法学曾经风靡一时。我国法制现代化发端于清末法律改革,继之以民国创制六法,当时正值德国法如日中天,故深受其影响。新中国的法学,在一定程度上继受前期法制现代化成果的同时,更受前苏联的影响。而以1922年苏联民法典为代表的前苏联民法又是以德国和瑞士的民法典为蓝本制定的,尽管它的制定贯彻着与西方法系完全不同的价值和目标。
前苏联的法学,从法学风格上讲,仍然是概念法学。但是,不同的是,它所采用的概念体系是由一套以意识形态教条为中心的独特概念和推理构成的,而且,这种概念体系的功利目标从根本上说不是以个人自由为价值理念的民事秩序,而是以阶级专政为价值理念的统治秩序。所以,在这套概念体系中,真正居于中心地位的不是(由法律现象归纳的)法学概念,而是(由意识形态衍生的)政治概念。
“文革”以后,中国法学复兴,其法学资料和方法又首先取自前苏联、日本和中国台湾,以及西欧的法典,以后才逐渐引进其他法系的成果。迄今为止,在中国法学界,特别是民法学界,概念法学的传统还是根深蒂固的。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那场起于70年代末,几乎持续于整个80年代的民法经济法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以“商品关系说”为代表的民法学派与以“纵横统一说”为代表的经济法学派,进行了旷日持久且影响深远的论争。现在,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这场论战实质上是社会的体制转轨和文化转型给中国法学带来的一次阵痛。论战的实质,从经济体制上讲,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从文化范型上讲,是权利本位与权力本位(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之争。现在,这场论战已经以纵横统一说的失势而告一段落,但都远未完结。就民法方面讲,自我总结的任务亦很繁重。因为,在这场论战中,民法学的学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求生存”(而不是“求发展”)的目标。而在求生存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在价值层面上较多地依靠了本学科在概念和逻辑方面的传统优势。因此,民法学在论战中不仅未能实现本学科理论上的中的创新与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自身的这种发展。
二、当代概念法学面临的挑战
从当前世界范围内看,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法典法系及其概念法学,其影响力有所衰退,而影响力显著增强的是英美判例法系。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变迁,打破了法律现象守恒的神话,从而使一个世纪以前法国人和德国人带着一劳永逸的愿望精心构筑的概念式法典城堡,在今日已难以见到其当年的风采和神韵。而英美判例法系的灵活务实作风,使它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始终保持进取的姿态和创新的活力。
要说判例法系和法典法系的区别,最根本之点,还在于其法律规范的重心不同,前者在于个别案件的公平正义,后者在于法律的稳定性。总的来说,判例法系的一套方法和技术,更能适应现代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而法典法系则显得比较僵化、迟钝。目前,在法、德等法典法系国家,原来的法典不仅历经修改、昔日尊容难驻,而且因不敷应用,不得不求助于日益增多的单行法规。而这些单行法规的具体性和操作性,同概念法学的那种抽象、缜密的学究气,显得格格不入。
与法典法系的概念中心不同,判例法系的思维重心在于“解决方案”“(solution)。基于”个别案件的公平正义“的立场,人们要求不同的案件(或曰,不同的事实背景)必须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判例法的操作方法,就是从以往的相同案件的判例中找出其中的解决方案,然后联系本案的背景和焦点,依据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确定本案的解决方案。如果法官认为昔日的解决方案同今日的价值理念不相符合,则不妨创立新的解决方案。如果法官遇到某种前所未有的事实背景,认为需要为之提供一个解决方案,那么他们不妨建立一种新的案由。如果昔日未受法律保护的某种利益,在今日被认为有保护之必要,亦不妨创立一个新的判例。通过新判例的问世,宣告一种新权利的诞生。此外,判例法要求法官在制作判决时充分阐述理由,故一份判决书往往无异于一本洋洋大观的学术著作。于是,法官成了职业的法学家,领导着法学研究的潮流。
法典法系和概念法学的困惑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前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冲破了法律价值单一性的桎梏,从而使那种排斥外来价值的封闭式规范体系和崇尚概念、拘泥概念的思维方式,难以适应多元价值并存沟通的时代潮流。
在西方,前现代社会价值单一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在社会经济领域片面追求效率价值(即财富增长的极大化)和个人权利自由价值,而无视社会公平和社会整体和谐的价值。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70年代以后,价值多元的局面开始出现。其主要表现是,一方面,通过社会化改良运动,树立社会公平和社会整体和谐的价值权威,将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置于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框架中加以调和;另一方面,以宽容和对话的精神,寻求主流价值同各种非主流价值之间的和平共存,使各种不同的社会意志能够平等地参与到利益与共的文明建设中来。
在东方,包括我们中国,多元价值并存取代单一价值主宰,也正在形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这种趋势使我们不能不认真考虑法律制度的观念更新、结构更新和思维方法更新。
判例法在过去的实践中确实表现出它在实现价值并存和利益调和方面的某些优越性。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而简单地断定21世纪将是判例法征服世界之世纪。由于判例法的操作系统依赖着一只庞大而素质精良的法官队伍和一套复杂精致、成本昂贵的诉讼机制,再加上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实在是一种难以继受的奢侈品。
介乎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的是斯堪的纳维亚法系,或称北欧法系。北欧法系是成文法系中的非法典法系,以单行的法规(Acts)为主要法律形式。北欧法系的基本风格是实用主义,即法律的制定以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故法律条文的设置不求体系完善,但求切实可行。在这种情况下,北欧法系的思维中心,既不是概念(concept),也不是解决方案(solution),而是规则(rule)。这就是说,人们在制定或者适用一项法律的时候,所考虑的问题是,在某个具体场合存在什么规则,以及如何解释和应用这些规则。这种以法规(Acts)为根据,以规则(rule)为中心,重在解决实际问题、满足实际需要的思维方法,就是北欧法系的基本特色。目前,在判例法系和法典法系的国家,单行法规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作用。单行法规的制定,既无需拘泥固有的概念和逻辑体系,也不受先例的约束,而主要是根据有关的法律政策(legal policy),即立法者对某一领域某些社会关系或社会问题的一般方针和对策。例如,瑞典的货物买卖法,是按照维护交易自由和提高交易效率的政策制定的;而它的消费买卖法,则贯穿着保护消费者和维护交易公平的政策。而这样的区别,在德国、法国的民法典里,则无法体现出来。
这种以规则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法规体系,对于现代社会关系的变易性和价值多元性,也有着较强的适应能力。而且,比起判例法系来,这种体系有着更大的可移植性。实际上,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领域的立法大都是单行法规。这些法规在制定和适用中表现出来的重实际求实效的务实作风,体现了中国社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文化格调,也代表了我国法制建设的未来路向。
三、中国民法要超越概念法学
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始终处于法文化冲突的困扰之中,追随德国法系的中国民法,由于受概念法学的束缚,长期以来一直被禁锢在法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尚未真正地成为广大民众手中的工具。学者们尽可以批评中国文化的落后的民众的愚昧,但缺乏文化土壤和民众支持的立法毕竟不能说是高明的。因为法律是为全社会制定的,是用以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的,它们不应该成为少数人闭门玩味的艺术品。 当年黑格尔曾批评孔夫子的哲学缺乏思辨,只能算作一种常识道德。如果孔夫子当时还在,他一定会对这种德国式的精神贵族的傲慢反唇相讥。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浩然之气。知天命、顺自然,从自身文化体验中获得的人生哲理,哪怕带有某种直观地或者经验的色彩,也丝毫不逊于那些故弄玄虚的形而上学和自寻烦恼的概念游戏。所以,中国民法要尊重中国的民族性,顺应中国的民情。
中国民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在一个长期以来缺乏发达市场制度和私权立法的国度里,建立现代意义上的民法,其困难可以想见。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和适应市场的能力,远比学者们想象的强得多。我们可以断言,现代民商法在中国生根发育的生态环境,实在比学者们想见的优越得多。所以,我们还不能把民事立法在实践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统统归咎于外部环境,而应该从法律和法学的自身中寻找一下原因。 我们要首先打破一个神话,就是以为从前移植进来的德国民法及其概念法学方法是先进的、科学的和不容置疑的。其次要打破的一个神话,就是中国人缺乏接受现代法治的文化基因。如果我们知道当代西方学者们是如何嘲讽、抱怨甚至声讨那给他们带来许多烦恼的概念法学,如果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在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中赢得了怎样的崇敬和推崇,我们就不会把超越概念法学看成是愚昧,也不会把尊重本国文化看成是保守。 当然,笔者并不反对制定我国的民法典,也不否定概念法学的学术贡献。所谓超越,不过是针对这类立法形式和法学思维方法对我们的束缚而言。而这种束缚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们自己的某种心理障碍或者认识缺陷。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博大包容的文化情怀,以及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更加高雅的文化品味,以便在包括本民族在内的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基础上,发挥中华民族素来具备的文化综合能力和文化创造能力。 超越概念法学,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超越法律现象守恒性和法律价值单一性的观点,以适应当代社会生活变易性和价值多元性的趋势。
超越概念法学,从法律形式和结构上说,就是要克服法典体系的封闭性和抽象性,在制定作为基本民事权利法的民法典的同时,重视制定适应经济生活实际需要的各种单行法规。
当代文学概念篇5
【作者】李富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兼壮学研究中心主任、学科带头人、研究生导师、博士、教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C9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2)01-
On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Minzu and the proper change of the pattern of Minzu study: the zhuang study for example
Li Fuqiang
Abstract : Analysing chinese ethnic ideas and the process of moulding of Minzu In the view of western theories of ethnic group and nationality,the author offer a proposal on the change of the pattern of Minzu study on the basis of re-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Minzu.
Key words:Minzu;Minzu study;Pattern
对中国“民族”概念内涵的讨论,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20世纪50、60年代,国内学界就曾对“民族”译名问题进行过讨论。但20世纪80、90年代兴起的对中国“民族”的大讨论,还是以其表述的时代性和讨论广泛性引起多方关注。如果说50、60年代对“民族”译名的讨论,是新中国在构建“民族”的过程中,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与中国实际的矛盾,且由于当时具体历史背景,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为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民族问题的论述的“读书会”的话,80、90年代关于“民族”概念的大讨论则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由于西方“族群”概念和理论的进入而引发的,其缘起和宗旨是中西学术对话。从1983年王明甫发表《“民族”辩》将苏联“民族/民族共同体”概念与西方ethnos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呼吁要对ethnos有一个精当的译称,以区别于“民族”i,到199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和《世界民族》杂志社共同举办“‘民族’概念暨相关理论问题专题讨论会”ii,2001年中南民族学院举办“族群理论与族际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iii,直至今日,有关“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按照王东明《有关“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一文的归纳,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iv:
(一)反对使用“族群”概念,或认为ethnic group指的就是‘民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阮西湖和朱伦先生为代表。阮西湖认为:作为单词,group有“群”的意思,但也有“族”的涵义,在国外人类学文献中,ethnic group一词就是指“民族”。“族群”这一术语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同体”的演进的各个阶段的表述,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献中也只有“民族”这一术语,未见“族群”的提法。另外,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是各国人类学者,在使用“ethnic group”这一术语时,其涵义都是指“民族”而不是“族群”,因此使用“族群”一词也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对当代社会人类群体的划分,同时也有悖于世界各国人类学者所表述的“人们共同体”的原意。朱伦认为,汉语中的民族与英文中的ethnic group并非是对等的概念,不能将其对等起来,“族群”更多的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事实上,将ethnic group译为“族群”没有什么问题,但在现实中使用“族群”这一概念是不恰当的,因为该词在西方近代民族学研究中含有歧视性。主要是指那此落后的异教徒、异种人民;同时,他认为各民族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是其正当权利之一,现实中使用“族群”取代“民族”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强调文化性、忽略政治色彩,为民族这种人们共同体在当今国家政治舞台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制造了障碍;另外,他还认为那种从避免民族问题政治化角度出发,主张使用“族群”而不是“民族”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当今世界“多族群国家”的实践并不成功,反而造成了许多国家现实中的民族矛盾。现实实践告诉我们,以“族群”概念替代“民族”概念,以“多族群国家”论来解释“多民族国家”,并按照传统意义上的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的“准标准”来建设“多民族国家”,在国际上己被认为是一种不成功的理论和不成功的实践。
(二)承认和肯定“族群”及其相关理论的价值,认为在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中运用“族群”概念并吸取国外学者关于“族群”构建的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对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发展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但是对现实研究中“族群”概念、理论的泛化则表不忧虑,持一些不同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民族”与“族群”二者并非是完全等价的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的“民族”概念有其特定的政治和政策含义在其中,中国的“民族’,是经过政府识别后确定的,因此用“族群’,来指称中国的56个民族是不妥的;2、“族群”与“民族”各有其特定不同的涵义,对于“民族”概念而言,文化不是其唯一的基准指标,两个概念实际上是居于不同的层次,故而两者不能互相取代和来用;3、在引进西方的学术术语和理论时,要对其产生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等进行客观的分析与梳理,同时国际学术对话也应是双向交流,不能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4、学术研究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实际,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在现实中采用何种概念、术语的背后,是复杂的社会群体利益,往往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建构、民族的权力关系等。
(三)认为族群这一概念更适合于我国民族问题研究实际的观点。持这类观点的学者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仅就学术角度考虑,认为族群概念及其理论更适合于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另一种则是从战略角度、政治角度出发,认为“民族”概念含有较强的政治含义,在西方话语体系中,民族(nation)往往与“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及“民族自决”相联系,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民族问题的政治化,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而“族群”概念所固有的淡化政治色彩的特点,更有利于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方面抑制本国各族群的“民族主义”诉求。
(四)认为“族群”概念的背后是弥漫在全球范围内的西方话语霸权,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平等的全球对话。当今西方国家借助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其文化价值观的战略行为,实际上“族群”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之争也是这样一个过程的体现。
综观此一轰轰烈烈的讨论,笔者以为,虽其对于促进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建树良多,功不可没,然其失误亦不可视而不见。至为要害者,乃其削足适履之弊,即以西方的概念、理论套用于中国之事实,而不是从中国的事实中阐发、提炼概念和理论,以补西方概念、理论之不足。其实,“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者的使命,不应拘泥于以西方的“族群/ethnic group”和“民族/nation”概念、理论诠释中国的“民族”,更重要的是在厘清西方相关学术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达成对中国“族群观” 和“民族”的本土认识。中国传统族群观与西方不同,“民族”概念虽是西方“舶来品”,但中国人在近代以来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按照本土的理解,赋予了“民族”不同于西方“nation”的涵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不揣浅陋,拟以西方族群和民族理论为观照,对中国族群观、“民族”的“塑造”过程及其内涵作一考察,在重新认识中国“民族”的基础上,对转变民族研究范式提出建议。
注释:
i王明甫,《“民族”辩》,《民族研究》1983年第6期。
当代文学概念篇6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概念的构成要素
一个国家必然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然而对于那些影响社会关系的运动,在我们看来,它有两个层次:一是本质层次,主要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二是运行层次,在这里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取而代之的是研究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方法、途径、机制等。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时代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哲学,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当代中国,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具体化,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理论、中国体系和中国形态。在这两个层次中产生的“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本身就包蕴有许多要素,在实际阐述时还要受到条件的制约,这些要素只能从对当代中国的个人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它们是即时共现的,要素之间没有任何距离,虽然互为区别,然而无法分离。离开具体条件的简单概念是没有的。凡是概念至少是双重的、三重的,甚至是多重的。概念因而有一个数目,由单个成分构成的概念也是没有的,因为即使是最初的概念、一部哲学赖以“起步”的概念,也有多个组成成分,而且靠它们获得规定。作为当代中国存在和发展的“总理论”和“总根据”,“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一个多重性概念,是一个复合性视域,这个概念有三个组成部分:“当代”、“中国”和“国家哲学”。“当代”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使中国社会革命、改革、发展有了特定的“主体”。在党未执政之前,它确定的革命战略属于前当代中国国家哲学。革命胜利后,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改变了,概念的性质及其理应回答的问题也改变了。所以“当代”是一个渐变过程。这涉及到一个概念跟位于同一平面上的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例如“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尽管有不同的形成过程和历史,但它们在“当代中国”这个平面上对接,相互印证,协调轮廓,组合各自的问题。“中国”作为“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实施的“平面”,它被当作真实的世界对待,这个世界并不真实,或者说尚未变为真实的世界,然而并不因此而不存在。中国人民的实践是当代中国国家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检验的标准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创造过程和自我设定、其理想性和现实性、其传授方法和本体论等都反映了中国的个性。王建均认为,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丰富的成果,是中国哲学思想之集大成。雍涛认为,邓小平哲学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态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形态出现的在中国的“应用哲学”。杨永庚在《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发挥指导作用的实证研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例》一文,分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黄微和田景仲在《科学发展观中的国家哲学》中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融价值观体系、本体论、国家体制论和国家伦理性于一体的国家哲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和不断变化着的中国国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规定为“国家哲学”。概念是由代表人物创立的,概念性人物来帮助规定其自身的性质。“概念不同于已经造就,静等人们去发现的天体,概念没有天空。它们必须被发明、被创造,或者准确地被创造出来,而且如果没有创造者署名的概念,便毫无价值。”[4]206概念总是带着署名人一起出现的,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实质”、笛卡尔的“我思”、莱布尼兹的“单子”、康德的“条件”、谢林的“潜能”、柏格森的“绵延”,等等。概念性角色操纵那些描写作者的内在性平面的运动,而且亲身参与作者创造概念的活动。概念性人物不代表哲学家,情形甚至相反:哲学家只包装了关键的概念性角色和所有其他人物,理论工作者必须负责触发他们的概念,以便为概念性人物施以斧正作出铺垫。哲学不断地引出概念性人物,国情的不断变化使概念本身形成了一幅新的思维图景,要结合时代的变革和中国的哲学传统,赋予实践不同的含义,创造不同的形态。尽管概念均有时间性,有署名人,有持之有故的名字,它们却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对“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概念也是在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必须更新、替代、发展。“当代中国国家哲学”家了解什么是概念,他们需要概念,懂得如何辨别概念,只不过很少为自己而现身,学者因而分别概括为:中国国家哲学、邓小平中国国家哲学、中国国家哲学、中国国家哲学。凡是创造活动都是独特的,纯属哲学创造的概念,尽管并非绝对的初始。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不断钻研哲学、运用哲学、发展和创新哲学,、邓小平、、都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社会,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所以应当称他们为应用哲学家、实践哲学家和中国国家哲学家。
当代文学概念篇7
目前,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的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是国内高等院校的一本通用教材,该教程第一编导论提出:建设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表示本书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如比兴、神思、意象、滋味、情景、意境等都有所融合吸收。应该说,该教材在中国古代文论构建中国特色方面的努力在同类型教材中较为突出,不过,该教材是如何吸收中国古代文论内容,古代文论在该教材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我想就这一问题,陈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作用。
1.横向结构上,古代文论知识的全面渗透。
多年来,《文学概论》课程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包含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等。这可以称得上是《文学概论》的表层横向结构。国内的《文学概论》教材大都围绕这几个部分而展开编写。《文学理论教程》即按此分为五编十六章。
而古代文论是古代文学理论家对文学的看法,也涉及对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和文学发展的种种看法,《文学理论教程》秉持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宗旨,有意识地在每个章节对古代文论的种种思想作了吸收。
如第四章论文学的文化含义,提到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论文学的审美含义提到了曹丕的“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陆机的“诗缘情”,钟嵘的“滋味”,刘勰的“情者文之经”,等等。第十章谈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举王弼的“言、象、意”三者关系;讲意境列王昌龄《诗格》中的三境说,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关于意境的概念。第十三章文学风格,谈创造个性,引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第十六章文学批评模式,以孟子的“知人论世”解释社会历史批评。
可以说,翻开《文学理论教程》,随处可见古代文论话语,其目的是用以解释印证文学理论的各个命题。古代文论因此成为了《文学理论教程》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讲,古代文论对于建构《文学理论教程》体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纵向结构上,古代文论对于概念原理阐述的积极参与。
如果把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称之为《文学理论教程》的表层横向结构。《文学理论教程》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深层纵向结构,即指文学理论原理得以透彻阐述的三方面内容。第一是关于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界定与阐述,这是《文学理论教程》的主体。第二是关于这些概念原理的历史由来、发展轨迹。许多教材在阐述文学理论内容时,会引述或介绍中外古今文论家对于文学活动的概括和总结、观念和思想,也即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
在《文学理论教程》纵向结构的三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如在第一方面内容即概念原理界定与阐述部分,第三章论文学活动的发展的多种因素,即引用了《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为之音”,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说明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诗论直接表达了文学活动发展中的一种代表性思想,并构成了原理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纵向结构的第二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所占比重更大。教材在阐述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之后,往往会引述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作为例证,其作用主要有二:首先,交代清楚文学理论的来源,说明其内涵。《文学理论教程》所要建立的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范畴相对抽象概括,对其理论的生成过程,以及概念本身的内涵都需要适当的说明,而古代文论的印证能够起到解释理论本身生成原由的作用。其次,深化理论,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对于同一个概念原理,历代文论家都作了不同的探讨,通过对不同说法的辨别理解,能确定教材中原理表达的科学与否。
纵向结构的第三方面主要是指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因为重心在文学作品,所以文论比重较少。
综上,古代文论纵向结构上对于概念原理阐述有所积极参与,既直接参与了概念原理的界定阐述,又起到了对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说明作用,印证说明方面起的作用更大。这也正是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具体作用体现。
二、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实际地位分析。
如上,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发挥着明显的作用。但冷静地看,古代文论在教材体系建构中又存在着一些问题,呈现出古代文论实际地位的尴尬。
1.古代文论在教材中零散存在的方式,不能显示古代文论的真正价值和魅力。
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从内容上说,主要偏于几个代表性的文论家的片言只语,和他们零星的文学思想表达。这些有限的概念术语的引述,多半是蜻蜓点水,谈不上系统,难以构建厚重的文论史的印象,没有展示知识的完整与深度。学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材料在书本中的实际意义。而且《文学理论课程》一般都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学生知识储备相对不足,对《文学概论》教材中夹杂的古代文论家的只言片语,很难消化吸收,这些文论内容只会成为理解文学原理的障碍。
2.古代文论主要以例证的形态出现,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
从作用上讲,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的三个构成部分,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一部分,即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建立。但纵观教材五编十六章及更进一步的章节小标题,用古代文论表达的内容少之又少,即古代文论直接参与界定、阐述概念原理的部分偏少。古代文论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即在理论阐述之后或过程中,作为例证起到解释文学理论来源和进一步说明理论的作用。由于缺乏必要的解释,很多古代文论往往是阐述文学理论时的点缀,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削弱了其在课程体系建构中的力量。
三、关于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作用的设想。
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袭用西方和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模式,以至于中国当代文论处于可怕的失语境地。所以,如何利用好古代文论,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成为一个阶段以来文艺理论工作者关注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只有在继承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民族特色,才不会在世界文论中失语。但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体系建构中的作用?
1.进一步发挥古代文论概念对于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解释作用。
古代文论语汇是古代文论家们对文学创作及作品特色的总结,它们本应该有着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能够真正起到印证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但是当这些文论术语分布于《文学理论教程》各个章节,则变成了散珠碎玉,零星分散,点到即止,缺乏说明问题的力量。要想真正发挥古代文论的作用,就应该对一些重要的古代文论进行解释,揭示古代文论概念的内涵、意蕴,交代古代文论的来龙去脉,展示其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从而使古代文论真正起到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并成为文学概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2.进一步发挥文论潜体系对于文学理论体系的印证作用。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潜体系。一是个别作家的论著具有体系或潜体系,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分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系统完备,体大思精。二是文论史上一些命题的阐述具有潜体系,如意境说经由《周易》的“圣人立象以尽意”、钟嵘的“滋味”、皎然的“取境”、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到王国维的“意境”,已从只言片语发展为有情有意有理论内涵的概念了。梳理范畴内在的演变和传承关系,又使之自成体系,以说明甚至参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等,对建设当代中国文论至关重要。
3.进一步将古代文论转换为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原理。
童庆炳说:“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转化’,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①
此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目前《文学理论教程》并没有做好这点,可能也有些古代术语已经转化为了现代术语在使用,但是却没有大量地转换。我的想法是尽量能使这些术语通过阐释后就能够进入当代文论的语境,成为能够解决当代文学实际问题的“范畴”,这才是“现代转换”。
传统文人对文学本质、创作目的、创作主体、作品本体、读者接受都有讨论,如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学开山纲领的“诗言志”,以及魏晋南北朝开始盛行的“诗言情”一直是中国文人论述中国诗歌本质的主要话语;如陆机“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李贽“童心”说等对创作主体想象与心境状态的描述;又如从《周礼·春官》、《毛诗序》以来对赋比兴的表述和解释,到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炼字篇、事类篇对于文学创作手法的表达;再如钟嵘“滋味”、司空图“四外”说、严羽“妙悟”、“兴趣”、王士祯“神韵’、王国维“意境”理论对于诗歌审美特质的概括,这些都是古人针对文学表达的理论观点,和他们进行具体诗文批评时所用的话语方式。这些皆可以转化为文学理论的标志性概念原理,成为文学理论的重要构成。
当代文学概念篇8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 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 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 “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当代文学概念篇9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当代行政学的重建和发展,行政文化作为一个外来的研究术语也被一同引入到行政研究的工作中。现在,行政文化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重要领域。不过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它还处在一个探索发展阶段,对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甚至行政文化的概念都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这无疑对行政文化研究的深入带来极大的困惑。本文针对目前行政文化概念的不一致认识,试图对行政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行政文化概念的提出
(一)文化―行政,当代行政学研究的新视野。早期行政理论和现代行政理论都是建立在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行政学理论尽管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其局限。70年代以后,这些思想受到了批判,胡格韦尔特在分析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后尖锐地指出:行政生态理论“象所有功能主义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一样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功能主义者忽视了把发达的世界和欠发达的世界之间历史的和当代的结构关系考虑在内”。这一缺陷“造成了特殊的不良后果[1]”。在这里,胡格韦尔特所批评的缺陷也就是缺乏具体对应的、实在的具体环境。行政不仅与环境相关,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环境,对任何行政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环境基础之上。
而要研究特定的、具体的环境下的行政问题,就必然地与文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文化高度体现了一个社会、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特殊意义,也正是特殊性的影响才使得行政研究的具体化要求显得格外强烈。当代西方管理学者也都强调:“管理不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文化,即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的一种文化。”至此,文化与行政的问题就成为当代行政学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行政文化也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被提出的。从此,文化作为一个新的角度,为行政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也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恰当的分析行政的方法。
(二)政治文化概念的诞生,是行政文化引起世人关注的逻辑原因。我们知道,行政学是从政治学分出来的一门学科,自从威尔逊的《行政学研究》以来,行政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才彻底独立出来。但是,在研究行政学的同时不能完全撇开政治学,它始终都是受政治的影响的。概括地说,就相对而言,行政与政治关系紧密;就被包含而言,行政与政治不可分割。因而,在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行政文化也相应地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目前我国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各种认识
行政文化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研究行政学的方法论,在我国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但是究竟行政文化是什么这一概念性的问题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概念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当代文学概念篇10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6-0036-02
一、概念在《高等代数》课程中的地位
数学从大方向上可以分为基础数学和应用数学,而基础数学又有三个分支:代数,几何和分析。大学的高等代数课程是一切代数学的基础,通过对它的学习,可以获得关于代数学最基本的知识、最基本的理论和最基本的思想方法。不仅如此,很多理论已经说明,高等代数的相关理论和思想方法已经渗透到其他学科,在数学、物理和化学等不同学科均有十分重要的应用。因此,学好高等代数,你将会终生受益。大家知道,高等代数课程中充满了各种定义概念,所有的理论都是从概念出发,诱导性质及计算方法,最终得到实际应用。由此可见,要想真正学好高等代数,对定义概念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是必须的,这是第一步。如果第一步没有走好,可想而知,高等代数就算没有入门,更不要说学得好了。然而,高等代数中的很多概念对我们大一新生来说还是比较抽象和难以理解的,这就需要我们的任课教师在实际课堂教学中以一定的方法来授课,不能只按课本讲,因为课本上定义的写法基本上都是最本质的,最精简的。
二、对概念教学的两点心得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要想使学生真正理解定义,教师必须以一定的方法来阐述概念,不能照本宣科。这里主要就笔者的实际课堂教学经验,粗略地谈谈自身处理概念教学的几点心得。事实证明,学生很喜欢这种处理方式,教学效果也不错。由于本人的学识有限,一些观点和方法肯定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恳请广大同行批评指正。
1.注意概念本身的深刻性,作合理地剖析、总结。众所周知,高等代数中的很多概念,课本上的叙述都是最简洁的,一般说来一个字都不会多;有时比较深刻。这就需要教师以自己通俗易懂的语言来剖析、解读和总结这些深刻抽象的概念。笔者的做法一般是根据概念中的关键词,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这个概念,让学生有个总体的认识,然后会认真分析概念中的关键点,让学生掌握概念的本质,最后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针对学生常常理解错误的地方,以“注记”的形式给概念加几条注解,防止学生犯同样的错误。最后以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让学生更进一步掌握概念。下面举一个具体的案例吧。就以行列式的概念作为例子吧!很多学校用的都是北大版的高等代数教材,它们的第一章是多项式。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后续课程的需要,很多教师的处理方式都是先上第二章行列式,等第四章上完后,再上第一章。这样一来,行列式就是学生遇到的第一个高等代数课程中的概念、定义也比较抽象复杂。笔者是这样来处理的,分如下步骤:(a)在黑板上写下完整的定义,然后开始讲解。(b)告诉学生,行列式这个概念中有个“式”字,式就是算式的意思,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行列式就是有一些行和列构成个算式,既然是算式,其结果是一个数值或者一个函数。分别举两个例子来佐证:一个是纯数字的,其结果是一个数值;一个是含有未知量的,其结果是一个函数。(c)然后问学生:两个阶数不同的行列式,其值会相等吗?进一步提示学生,在中学阶段我们学过很多算式,值相等的算式一定一样吗?这个学生肯定知道。然后补充说,行列式归根结底是一个算式,所以值相等的行列式未必一样,阶数也未必相同。然后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这样学生就会真正认识到行列式的值与其阶数无关,这也为将来学习到矩阵时理解与矩阵的区别埋下伏笔。(d)把(b)、(c)整理成叙述性文字,以注记形式写出。(e)为了让学生理解行列式的定义:a11 a12 …… a1na21 a22 …… a2n…… …… ……an1 an2 …… amn=
■(-1)■a■a■…a■,以3、4阶行列式作为实例,具体地写出表达式中的每一项,并分析每一项的组成和结构,让学生准确具体地理解上式的内涵。
2.注意概念本身的抽象性,适当地用合理的比喻。高等代数中的很多概念非常抽象,但从数学层面,学生一开始很难全面正确地理解、掌握。这就要求任课教师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学生容易接受的一些“合理的比喻”,让学生快速准确地掌握概念。笔者还是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说明。以向量组的极大线性无关组为例:向量组是高等代数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极大线性无关组的概念是一个难点。粗略地说,设A是一个向量组,B是A的一个子向量组,如果B满足如下两条:(1)B本身线性无关;(2)再从A中拿一个向量放到B中,B就线性相关了。则称B是A的一个极大线性无关组。初学者对这个概念理解的要是不全面的话,会影响到后面相关概念和性质的理解。比如一个向量组的极大线性无关组的取法不唯一性、极大线性无关组中所含向量的个数,即秩的不变性等。笔者为了让学生更轻易地理解,做了如下比喻:把整个向量组比作中国;极大线性无关组比作中央领导人。对应于条件(1),就是说中央的各位领导人各负其职,互相不能取代;对应于条件(2),就是说中央一共就那么多的职位,已经没有空缺了,你硬要再塞一个人进来的话,只能会出现某两个人干一份差事的情形,可以相互取代,不再是各负其职了。当然,做了这样的比喻以后,对于极大线性无关组的取法不唯一性也很好说明了:因为中央领导人是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当然另外一帮人也可能当领导人,或者说每一届都有不同的中央领导人。而对于极大线性无关组中所含向量的个数的不变性更好说明了,不管那一届的领导人,人数是一样的,因为职位数是不会改变的。
当然,对于概念的教法,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方法。我这里只简单地说明了我常用的方法,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数学系几何与代数教研室代数小组.高等代数[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三版).
[2]吕家凤.浅谈高等代数课程中概念教学的若干心得[J].教育教学论坛,2012,(4).
[3]郑君文,张恩会.数学学习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
[4]刘安君,孙全森,汪自安.数学教育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5]张奠宙,唐瑞芬,刘鸿坤.数学教育学[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6]魏献祝.高等代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7]章如磊,韩梅.变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J].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297-300.
当代文学概念篇11
“全球性”与“现代性”
“现代性”是“全球性”问题中的一个关键词,这两个概念关系之密切,以至人们提起一个,就自然会想起另一个。问题在于,“全球性”是一个空间概念,是对于全球范围内人类生存状态趋同性的界定;“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对于“过去—现时—将来”的时间链中“现时”这一时间段之特点的概括。那么,二者何以能够如此密切地相互交叉、彼此融通呢?二者交叉融通的关节点何在呢?
当今滚滚而来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冲决一切制度、地域、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固有差异,拆解着以往矗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种种有形或无形的樊篱,将经济、生产、流通、政治、思想、文化纳入一体化的体制:而这一切恰恰都被确认为“现代性”的表现。鲍德里亚说:“(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它将自己与传统相对立,也就是说,与其他一切先前的或传统的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反对传统文化在地域上或符号上的差异,它从西方蔓延开来,将自己作为一个同质化的统一体强加给全世界。”(注:鲍德里亚:《遗忘福柯》,见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论》第145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这就是说,当今全球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性地推行同质性、排斥异质性,重建一种新的文明模式,这本身就意味着对于传统的否定和排斥,而这一点恰恰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据考证,“现代”(modern)一词早在古罗马和中世纪就出现了,而“现代性”(modernity)一词的使用则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牛津大词典》确认,英国人首次使用“现代性”是在1627年,它被用来指中世纪之后的“现时代”的本质特征。法国人使用“现代性”一说与启蒙运动有关,它所张扬的是用理性来评判一切的启蒙精神。在德语世界中尤金·沃尔夫首开风气,1886年在一次讲演中首次使用了“现代性”这一说法,后又在1888年发表的《最新的德国文流与现代性原理》一文中,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界说,使之广泛传播开来。从词源学上追溯,“现代性”这一生造的德语新词,大概是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流行概念中衍生而来。总之,“现代性”一词上承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变革精神,与生俱来地表现出对于以往传统的否定性、叛逆性和批判性,在以后的重大社会变革时期往往成为人们的一种价值寄托和精神追求,一次又一次地浮出海面,成为人们倍加关注的热点。
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还有“当代性”这一概念。所谓“现代”、“当代”从表面看都属于时间概念,用以表示现时、当下的时间存在。但从根本上说这二者并不仅止是一种时间性的界定,它们与“世纪”、“年代”、“年月日”之类时间概念迥然不同,如果说“世纪”、“年代”、“年月日”等时间概念是单纯的、中性的、不带任何价值倾向的话,那么对于这二者显然就不能这样说了,在人们使用“现代”、“当代”这两个字眼时,分明较之上述单纯的时间概念多一层价值判断的色彩,那就是立足于当下、现时而对世界所持的一种态度和立场。正因为如此,所以“世纪”、“年代”、“年月日”之类时间概念无所谓什么“性”,而“现代”、“当代”则合乎情理地扩展为“现代性”、“当代性”,并且为人们所广泛使用。
然而“现代性”与“当代性”又有所区别。“当代性”是指从当下、现时出发而对世界抱有的一种价值态度,体现着当代人的思想观念、生存状态和趣味风尚,从而“当代性”的核心是一种当代精神,它是用当代精神去观照、理解和处理问题,无论对象是什么,哪怕是过去的、古代的对象,只要为这种当代精神所照亮,便获得了“当代性”;反之,如果缺少了这种当代精神的烛照,即使对象是现在的、当代的,也谈不上什么“当代性”。因此“当代性”并不专对“传统”而言,它可以加诸任何对象之上,是对任何对象都生效的。当然“当代性”也以“传统”为对象,但它对于传统并不一味采取激进的否定立场,当代精神的体现有时也许恰恰在于对传统的肯定和认同,远如文艺复兴时期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学术的“复兴”,近如晚近以来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振兴和弘扬,无疑都是对于“当代性”的最好诠释。
“现代性”则不同,它生来就表现出对于传统的怀疑、拒斥和反叛态度,其核心就是一种争天拒俗、刚健不挠的叛逆精神,而它就将这种叛逆精神视为当下、现时应有的生存状态,甚至是人们所应追求的至上境界、所应恪守的唯一准绳。从而“现代性”并不是在时间上与“古代性”相呼应的概念,而是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性”相对立的范畴。对此法、德、荚的当代学者所论甚夥,哈贝马斯说:“现代性反叛传统的那种规范;它所依赖的是,反叛一切规范的经验。”(注:哈贝马斯:《现代性: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安东尼·吉登斯说:“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现代性把极端的怀疑原则制度化”(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3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乌尔里希·贝克也说:“现代性意味着一个传统确定性的世界正在衰竭,正在被取代”(注:Ulrich Beck,World Risk Society,Cambridge:Blackwell,1999,p.10.)。
从以上论述殆可达成这一看法,如果说“当代性”是从当下、现时出发而倡言一种当代精神,从而消除了单纯时间概念的价值零度的局限性的话,那么“现代性”则因张扬一种对于传统的反叛精神而秉有更加强烈、更加激进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取向。
正是在这一点上,“全球性”与“现代性”达成了一致。因为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遭遇最严峻
当代文学概念篇12
关键词:尊严;生命伦理;自主性;工具理性;人性迷失
中图分类号:B82-0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5)03-0001-06
The Value of the Concept of“Dignity”in Bioethics
WANG Yunling1,GAO Jianguo2
(1School of Medicine;b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012,Shandong,China)
Abstract:Because of the ambiguous implication of“dignity”concept,scholars like Macklin and Hoerster held the view that“The concept of‘dignity’is useless”and they argued to remove the lexicon“dignity”from the ethics vocabulary.This point of view was opposed by a number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They held that the concept of“dignity”cannot be replaced by such concepts as“autonomy”because the concept of“autonomy”merely has similar meaning to“dignity”and it cannot totally cover the connotations of“dignity”.The value of the concept of“dignity”lies in that it can express the value connotation which cannot be expressed by any other words;it is the core value of Bioethics;it can help people fight against the spread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save them from the lost human nature.
Keywords:dignity;bioethics;autonomy;instrumental rationality;lost human nature
“尊严”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这导致了学界对这一概念有无价值的争议。人们对“‘尊严’到底指什么?用它来辩护的人类重要价值是什么?在现代医学科技文化中‘尊严’是否是一个必要的概念?”等问题莫衷一是。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医学科技文化中许多与医学新技术应用相关的道德讨论几乎都与尊严相关,如对克隆技术、人工生殖技术、死亡标准等问题的讨论。本文试图在回顾相关学界争议的基础上,对“尊严”概念在生命伦理学中的价值予以探析。
[BT1]一、“尊严”概念的存废之争
当我们回顾人类文明史时会发现,“尊严”曾经是人类为之努力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今天,让每个人都享有尊严,不得无故侵害人的尊严,早已成为文明世界的共识;人类之间和平交往,反对迫害与虐待,尊重人的尊严,共享稳定与和谐,已经深入人心。而这些都是因为尊严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健康发展、防止自我毁灭的精神基础。承认人人都享有尊严,这是人类在生存斗争史上所取得的一项巨大成果。然而事实上,当人们认真考察什么是“尊严”时,却意外地发现,“尊严”概念极其抽象、模糊和难以琢磨。人们在使用它时似乎都知道它意指什么,但是真正需要对其内涵进行明示时,却发现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事实上,当不同的人把自己对“尊严”的理解放在一起比较时,很可能发现大家所讨论的并非同一种东西。正因如此,一些伦理学者向“尊严”发难,认为这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应该将其从现代伦理学词汇表中剔除出去。
[BT2](一)“尊严”概念无用论的挑战
基于“尊严”概念含义的抽象性而认为它“无用”并主张抛弃它的人中,露丝・麦克琳(Ruth Macklin)是最典型的一个学者。2003年,她在《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上发表《尊严是无用的概念――它并不比尊重人或人的自主性有更多含义》一文,主张从医学伦理学中删除“尊严”概念。麦克琳认为,“尊严”概念并没有给生命伦理学提供更多的东西。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回顾了“尊严”概念进入生命伦理学的历史,认为这一概念与美国社会在道德和法律领域对人的自的强调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美国官方认识到病人“事先做出指示”(make advance directives)的重要性,并制定了此类法规。例如,1976年的“加利福尼亚州自然死亡法案”的条文所阐述的语境便涉及到“尊严”概念的使用:“立法机关由于知悉患者拥有享有尊严和保护隐私的权利,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应该意识到,成年人有权利做出文字指示,以便使医生知道,在病人生命末期应该维持还是撤除生命支持措施。”在麦克琳看来,此种语境中的“尊严”概念并没有超出尊重自主性的含义。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麦克琳在其文章中还提到了许多其他例子,如医学生利用新鲜尸体做插管之类的操作练习。生命伦理学家可能会谴责此种做法冒犯死者尊严,但麦克琳却认为这和尊重自主性毫无关系,因为此时医学生并不是在一个人身上进行练习,而是在没有生命的尸体身上练习。人们有理由担心死者家人的想法――如果他们知晓自己亲人的尸体受到那种对待的话。但在麦克琳看来,此种担心与死者的尊严毫无关系,而只是与死者家人的愿望有关系而已。在其他情形中,如关于生殖技术和遗传学的伦理学问题,麦克琳认为“尊严”概念会在个别地方获得意义,但它并未超出理性个体进行思考与行动的能力(尊重自主性原则)。因此,“尊严”概念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其含义模糊,并没有比已有表述给出更精准的表达,因而也就不能提供更多具有实质性含义的东西,从医学伦理学中删除它不会有任何损失。
此类看法并非麦克琳的突发奇想,她也不是唯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德国哲学家赫斯特(Norbert Hoerster)也持有与之类似的观点。2002年,赫斯特指出,“尊严”在哲学、法学和伦理学领域中都是一个重要概念,但是它缺乏一个清晰的内涵。这种情形是很奇怪的。不要忘记,在德国,“尊严”被看作全部社会秩序之最高价值,即使如此,德国联邦也没有对“尊严”进行定义。结果,“尊严”概念实际上被滥用了,从而造成了这一概念的贬值。在涉及某一问题的争论时,支持者和反对者可能都会诉诸“尊严”,如对安乐死的争论就是如此。人们就很难想象这个概念能够发挥其应有的社会规范作用,很难想象它能有效地判定和调节社会利益冲突。最后,“尊严”概念很可能会沦为一个“空洞的公式”或一句“无描述性内容的口号”,甚至成为“意识形态的武器”。如果是那样,还不如干脆从现代伦理学词汇中将其剔除。
[BT2](二)学者们对“尊严”概念无用论的回应
“尊严”概念无用论在学界引发了激烈争论,许多著名学者都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刊发麦克琳文章的《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30多篇快评,许多生命伦理学学家卷入争论,甚至包括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委员会的专家们。这表明,“尊严”概念无用论不但是一个学术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议题。这一议题触动了伦理学家和政治家们的敏感神经。
在这场讨论中,绝大多数学者承认,“尊严”概念的确存在含义不清晰的问题。但是,面对这一问题,简单的抛弃并不是好办法,设法澄清其含义才最重要。学者们从三个方面对麦克琳的思想做了批判。首先,人们不能以“模糊性”作为抛弃一个概念的理由。许多概念含义都是很模糊的,在不同的道德共同体中和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可能有不同的阐释,然而它们不但未被抛弃,实际上还被频繁使用,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如平等、正义、善、公正等概念便是如此。“尊严”其实也是这样的概念。其次,含义模糊并不一定意味着概念无用。就“尊严”概念而言,在许多领域,如学、法理学以及生命伦理学领域,它都是相当有用的,往往被用来表达丰富的思想,这样的概念不应被随意抛弃。对于这样的概念,人们要做的事情是对其进行更加精致和细密的哲学分析和理论探讨,而不是简单抛弃。最后,“尊严”概念和“尊重自主性”也有差异。“尊重自主性”主要指对人类理性的尊重,但对那些缺乏理性的人类个体,我们允许使用人制度,因此可以不再考虑这些个体的自主性。例如,深度昏迷病人、休克病人以及婴幼儿。但是,我们不能因这些个体缺乏理性而不考虑其尊严,随意处置甚至侮辱他们。相反,我们必须认真看护他们,敬谨地对待他们。“尊重自主性”与“尊严”不能等同的情形很多。例如:一个人的自主性未被违背,却可能有失尊严;一个人的自主性受到了侵犯,却可能未失尊严。前一种情形,如那些来自贫穷地区,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得到医疗服务的病人;后一种情形,如一个自杀者被强制送医等。可见,“尊严”概念与“尊重自主性”可能在含义上有重合之处,但两者并不等同。
西方学者除了对“尊严”概念无用论提出批评意见,也对“尊严”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探索。一般来说,尊严意味着“某种值得赞誉或崇敬的东西”,或者是某种杰出或非凡的特性。在“尊严”概念的历史沿革中,康德在理论上做出的贡献最为重要。康德关于人之所以都拥有尊严是因为他们都拥有理性的自觉,人的尊严与人本身的固有价值相联系的观点对当代“尊严”思想具有重要影响。事实上,无论“尊严”概念的含义如何演变,“尊严”概念都应该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念。
关于“尊严”概念是否有用,是存是废,中国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学者大多肯定“尊严”概念在各个学科领域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比如,关于“人的尊严”到底在生命伦理学中有何用途的看法,韩跃红就认同生命尊严应当成为现代生命价值观的内核的观点。张国安也坚持认为“人的尊严”乃生命伦理学之重要概念,具有不可替代性;“人的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基本价值追求,它在其概念体系中处于较高层次,统摄其他概念。甘绍平明确表示:“研究尊严理念,从而更好地坚守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是今天人们的一项重要职责。”可见,国内学者大多对“尊严”概念持肯定看法。
[BT1]二、“尊严”概念的价值
尊严”概念的价值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HTK](一) “尊严"概念所代表的价值,人类不能使用其他语言来进行表达[HT]
持“‘尊严’概念无用论”观点的人认为,“尊严”这一概念完全可以使用其他语言来代替,如“人权”或“人的自主性”等。在他们看来,“尊严”概念并未提供超出这些概念的更多东西。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别进行细致分析,就会发现“尊严”概念的涵义不但区别于其他概念,而且实际上内涵更为丰富,它所反映的某些价值无法使用人类的其他语言来进行表达。
许多人以为在某些场合中“尊严”概念完全可以被“人权”与“人的自主性”这两个概念来代替而并不损失任何含义。事实上,“尊严”概念和“人权”与“人的自主性”都仅仅只是含义交叉的关系,并不能互相代替使用。
首先,“人权”与“人的自主性”这两个概念都只含有“尊严”概念的部分涵义,二者都不能完全包容“尊严”概念所含有的伦理意蕴。例如,孟子讲:“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艰难境遇最能展示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处于即将饿死的境遇中却拒绝嗟来之食,是有骨气的表现,是一种做人的尊严。然而,有骨气与“人权”和“人的自主性”之间却并没有必然联系。孟子把这种骨气称之为“浩然之气”,其“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人权”与“人的自主性”这两个概念显然都不能包容这种含义。又如,英国学者泰德提到一种未被侵犯人权,也没有被违背自主性的典型情形,就是那些因身体退化失能又缺乏儿女照顾而不得不孤单地在养老院里生活的老年人。这些人早已退出社会生活,终年没有人探望,他们常常产生被社会和家人抛弃的感觉。虽然政府的高福利制度使他们没有衣食之忧,但是他们感到缺乏“尊严”。对这些老年人而言,缺乏尊严有何伦理意蕴?这伦理意蕴便是:这些老年人对国家和社会来说已经失去价值,因而他们自己丧失了生活的意义感。这一伦理意蕴显然与“人权”和“人的自主性”之类概念的意蕴完全不同。
其次,由于涵义交叉,“人权”与“人的自主性”中的某些涵义实际上也无法被“尊严”概念包含。例如,当一个人人权受到侵犯时,或者当其“自主性”被剥夺时,很可能与其“尊严”毫无关系,甚至反而展示了个人的“尊严”。人权受到侵犯的情形,如一个人因坚持正义而为恶势力所不容,惨遭杀害,其人权受到侵犯,却并未丧失“尊严”。为正义事业献身倒是一种英雄壮举,反而展示了个人“尊严”。“人的自主性”被剥夺的情形,在学上有一个典型案例,足以说明人的自主性与人的“尊严”并非同一个问题,这个典型案例就是法国的“投掷侏儒案”。1994年,法国奥日河畔莫桑镇(Commune de Morsang-sur-Orge)镇长了一个禁止在这个镇的舞厅进行“投掷侏儒”演出的命令,认为这种演出伤害了人性“尊严”。然而,当事人认为镇长的决定没有道理,就诉至地方行政法院,请求撤销镇长禁止“投掷侏儒”演出的命令。案件反复审理,最后上诉到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最终作出了该行为“与公共秩序(order public)不相容”的裁定。当事人认为,“投掷侏儒”演出乃是其自主自愿选择的行为,而镇长的禁止命令违反了其自主性。可是镇长却认为,不允许“投掷侏儒”表演是维护当事人的“尊严”。在这个案例中,当局诉诸“尊严”,而当事人诉诸“人的自主性”,两者的结论与主张截然不同,表明“人的自主性”与“尊严”有时并非同一回事。这种情形也典型地体现在发生于中国某地的“女体盛”事件上。2004年,某娱乐公司推出“女体盛”,以女大学生的身体当食器盛菜,引发争议。随后,某妇联发表文章怒斥“女体盛”侵犯女性“尊严”,而当事人却称行动出于自主选择。可见,尊重人的自主性并不一定意味着尊重人的“尊严”。
所以,“人权”和“人的自主性”与“尊严”概念在含义上有实质不同,尽管某些情况下其含义确实有交叉,但彼此并不能互相代替。“尊严”概念所表达的某些重要价值确实不能在其他概念中找到或用其他言辞来确切表达。当然,到底何种重要价值只能通过“尊严”概念来表达,也许还需要深入研究,但是毫无疑问,“尊严”概念是不能被其他概念取代的。概念含义模糊的情形在各个学科中都是很常见的,如法学中的“权利”、哲学中的“理性”等概念,都是如此[ZW(DY,7]
以“权利”概念为例,在法学界,对它的解释方法纷繁复杂。夏勇在谈及此种复杂性时引用康德的话说:“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什么是真理?’那样使他感到为难。”而费因伯格则在其著名论文《权利的本质与价值》里断言:给“权利”概念下一个“正规的定义”是不可能的。1991年出版的弗雷泽《权利》一书在论及研究“权利”概念的途径与方法时说:“在政治理论里,权利已经成了一个最受人尊重而又确实模糊不清的概念,想在原理上阐发权利概念所代表的观念,与阐发诸如平等、民主乃至自由之类的观念,几无二致。”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8页。
[ZW)]。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至今仍在不断探讨中,甚至每一项涉及这些概念的具体研究都要首先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
[BT2](二)“尊严”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念
与医学伦理学不同,生命伦理学并不只是关注行为规范,而是要研究作为行为规范之依据的价值观念,如“正义”“平等”“德性”“权利”“义务”等,但这些观念中所体现的核心价值乃是人性“尊严”。诸如安乐死、人工流产、放弃治疗、器官移植、基因工程、人工生殖等当今生命伦理学研究中的主要生物医学议题几乎都与“尊严”相关。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当代生物医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有可能从根本上触及传统价值,而某些传统价值乃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其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秩序的根基而不可被动摇。人性“尊严”就是这样一种基础价值,是当代生命伦理学辩护的核心价值观念。
显然,把“尊严”作为生命伦理学研究和辩护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性“尊严”思想的萌芽出现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德尔斐阿波罗神庙上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就是先贤对人性“尊严”思想的哲学启蒙。而近代启蒙运动以来,人性“尊严”思想越来越为哲学家们所关注,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思想家都对“尊严”思想有过深刻阐述。
康德的“人是目的”的目的论思想奠定了现代人性“尊严”观念的理论基础,并使“让人拥有尊严”越来越成为近现代人类社会的重要奋斗目标。人类能够追求“尊严”,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是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的重要标志,是人类自尊、自信、文明与开化的体现。就此而言,在现代生物医学科技背景下,在人性“尊严”面临工具理性威胁的道德境遇中,生命伦理学把“尊严”作为核心价值来研究并非来自某些聪明人的偶然灵感,而是合乎文明社会发展逻辑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现代社会发展和文明发展的支柱与结果。
[HTK](三)“尊严”概念帮助人们对抗工具理性,拯救人性迷失[HT]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的日常语言科学化,生活习惯科学化,甚至社会风俗也已经“科学化”。例如,传统社会中的节日走亲访友已经部分地被短信祝福和视频聊天代替。如果说这些改变还只不过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科学技术作为工具理性的一种依赖,而并没有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尊严”)造成更大影响的话,那么,在医学领域,人民便能切实感受到科技作为工具理性对人们生活影响的严重程度,因为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医学对人类生活的过多侵入。确切地说,这是指人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医学化现象。例如,我们以医学理论为依据来指导和变革生活方式,不吸烟是因为烟草中的焦油、尼古丁等会伤害我们的肺;少喝酒是因为酒不但会让我们产生酒精依赖(一种精神性疾病),而且可能使我们的血压升高,等等。而当我们的身体发生变化或者不适之时,我们不是求助于生活经验或者文化传统,而是使用医学语言来解释。这种情形在传统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就此,恩格尔哈特教授有过一个重要评论:“医学使实在医学化,它创造了一个世界。它把一些问题翻译成它自己的术语。医学塑造了经验世界由以形成的方式,它为我们限定了实在。人们所具有的困难由此可被了解为病症、疾病、畸形和医学上的异常,而不是被看作无故的烦恼、正常的疼痛或魔鬼附身。医学问题是一系列现象,人们把它们看作是适合于医学的评价、说明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或治愈的。”之所以会这样,显然是现代医学建制化发展的逻辑结果,医学在逐渐控制人类的生活,并成为人类当代社会生活的一种范式。通过这种范式,人们根据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对生活给出种种解释问题的医学预设,如身体胖被解释为营养过剩,个子过高被解释为垂体问题,等等。传统社会中无需烦恼的问题在今天则成了病症。这样,现代医学就创造了一种超越经验的社会实在,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则不得不在科技权威面前接受这种实在。据此,当某一问题被解释为医学问题时,医学实际上就在决定着人们的生活预期,人们的命运就必定受到医学的影响。事实上,这表明现代科技发展正在导致人性异化,威胁着人性“尊严”,而这正是康德曾经担心的问题。
这是一种生存困境。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困境并对其进行了深刻反思。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科学和工具理性已经与政治相结合,深刻地奴役着人和自然界。马尔库塞使用了“单向度的人”这个概念来指称那些在现代科技背景下丧失了否定性和批判精神的人。弗洛姆则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商品化和物化的情形称为“人性异化”。他们所揭示的人类生活情形正是人类在现代科技社会面临丧失“尊严”之危机的情形。这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所面临的一种深层生存危机。
如何在现代社会拯救人性的迷失?弗洛姆揭示了人不同于动物的一种重要特性,即人有回忆过去、展望未来的能力,有使用符号的能力,有理性地理解和规划世界的能力,具有巨大而丰富的想象力。我们把人的这种特性叫做“反思性自我意识”,是人与动物的标志性区别。当人秉持这种反思性自我意识并能够按照个人意愿自由行事时,人就拥有了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能力。这是人类的一种高度主体性与自我超越性。只有在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中,人才能体悟人之为人的高贵与幸福。根据马斯洛的看法,人的最高需要就是赢得自尊。这种需要会成为一个人行动的动力,也就是争取“尊严”的动力。然而,在当代科技背景下,此种动力却在面临着不为人所自知的消解的危险。为此,当代生命伦理学家把“尊严”概念所代表的价值作为现代社会人们拯救人性迷失的行动目标,是恰当的。
可见,“尊严”概念在当代生命伦理学中极为重要,它代表了人类使用其他语言不能表达的重要价值,是生命伦理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帮助人们对抗工具理性的泛滥,拯救人性的迷失。基于这些理由,人们完全可以肯定“尊严”概念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及不可替代性。当然,由于人们至今对它的研究尚存不足,因此其含义还不是非常清晰。然而,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尊严”概念不但可以认识,而且可以有很清晰和准确的含义――去认识并清晰地界定它,这正是伦理学家的责任。
参考文献:
[1]
甘绍平.作为一项权利的人的尊严[J].哲学研究,2008(6):85-92.
[2]RUTH MACKLIN.Dignity is a useless concept:it means no more than respect for persons or their automomy[J].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03,327(7429):1419-1420.
[3]NORBERT HOERSTER.Ethik des Embryonenschutzes[C]//Ein rechtsphilosophischer Essay.Stuttgart,2002:24.
[4]韩跃红,孙书行.人的尊严和生命的尊严释义[J].哲学研究,2006(3):63-67.
[5]张国安.人的尊严与生命伦理学[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25(6):71-76.
[6]Win Tadd.给予老年人体面的照护:为什么尊严很重要――欧洲经验[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11):6-9.